太阳下的风景——黄永玉与他的文学行当
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
文学让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
我不明白写文章用秘书用录音机用电脑,怎么还能写出来……叙述回忆录的时候需要秘书,文学是不行的,它有文字语句的讲究,有上下句音韵的节奏,有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够酝酿出来的那种情调和气氛,它不能光是讲故事,它要进入情境进入角色,要集中精神,鸦雀无声地促涌出来。
——黄永玉
01两个场景的历史呼应
故乡,文学的摇篮。
1937年秋天,南方的厦门。12岁的黄永玉,自家乡湘西凤凰漂泊而来,就读于厦门集美学校。开学之日,穿上校服学生装去照相。他给家里寄去照片,同时,还送给弟弟们一首诗:
太阳刚起了光芒
在我的床上
引起我的思潮
我不愿再在人海中彷徨
只要回到我的故乡凤凰
同着我那
永厚、永前、永福、永光
过着顽皮的景象
这首思乡诗,是迄今为止所知黄永玉最早的文学作品。
热爱文学,倾心文学创作,无疑是故乡对黄永玉的另外一种赐予。
黄永玉自幼感受着故乡漫溢而出的文学气息。在凤凰成长的十二年,与文学相关的诸多元素:知识、情感、修养……一日日渗透于心。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母又均为接受新文化时代的知识分子。黄永玉识字很早,两三岁即开始背诵古诗,继而背诵四书五经。正是在故乡与家庭的这样一种氛围里,黄永玉与众不同的多方面文学能力得以孕育、滋长。
1951年,当黄永玉初现创作才华时,作家汪曾祺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认为黄永玉身上具有难得的天赋。由画谈起,又不仅限于此。他写道:“永玉是有丰富的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记性’,他对事物的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的不竭的创作源泉。”黄永玉后来的创作拓展,他在绘画与文学诸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生动而丰富地诠释了汪曾祺的这一见解。
如果将黄永玉在1937年写下思乡诗的时刻,作为他的第一个文学场景,那么,时隔75年之后,另一个文学场景出现在我们面前——《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黄永玉晚年正在创作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名叫序子(小名“狗狗”),原型即作者本人,小说中的朱雀城,即凤凰古城。小说当然有虚构成分,但它们显然是基于黄永玉儿时生活体验的再创造。
黄永玉萌发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很早。40年代初,刚刚20岁时,他在福建漂泊期间第一次开始创作,提笔写过片段。战争年代,生活所迫,写作无法进行,他只好放弃。60年代中期,他再次想到这部小说,欲重新提笔,但“文革”突至,又未如愿。1990年前后,他终于有机会静下心续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完成十几万字后一度停笔。2008年再度续写。作品一边写,一边于《收获》连载。从85岁,一直写到93岁。
显然,《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贯穿黄永玉一生的美丽的文学梦想。在绘画艺术领域,他已蜚声中外,却对此远远不满足,即便到了80岁,如同青年时代一样,依旧拥有文学的激情和雄心。在这部小说已经完成的篇幅里,黄永玉以具有现代汉语之美的个性叙述,描写自己儿时经历,借此勾画出广阔社会背景下的历史沧桑。
纵观文学史,绝大多数文学家早在年轻之时就有了明确的文学自觉、激情与目标,创作高潮也很早得以形成。有着艺术家身份的黄永玉则明显不同。与文学结缘70年,但他的主要文学创作,他被视为一位文学家,则是在年过半百之后。他以自己的独特姿态,走着一条与其他文学家不同的途迳,其呈现方式也颇有不同。
迄今为止,黄永玉文学道路已长达70余年,试将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尝试与沉寂,从40年代初至1963年左右,约20年;
第二阶段:私下写作,从1964年至1976年前后,约12年;
第三阶段:自觉与丰收,从1977年至今,整整40年。
02尝试与沉寂:谁人能言得与失?
诗歌是黄永玉最早的文学尝试。
据黄永玉回忆,他在报刊上开始发表诗歌,是在1943年左右。目前,我发现的他早期公开发表的诗歌有三首。《风车,和我的瞌睡》,1947年8月创作于上海;反映香港电车工人罢工事件的长诗《无名街报告书》,发表于1952年;与《无名街诗报告》同期,发表与罢工事件相关的另一首诗《一定再见》。
从诗开始,黄永玉早期的文学尝试随之扩展至电影剧本、散文、文艺随感等不同体裁,主要集中于1947至1953年。
1948年从台北抵达香港后,他发表了散文《台湾归来记杨逵》。1950年,他回湘西旅行,为香港《大公报》撰写长篇游记《火里凤凰》在副刊连载,可谓早期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散文作品。
黄永玉第一阶段最有广泛影响的作品,是他的电影创作。1951年,黄永玉在香港为长城电影公司创作两部电影剧本:《儿女经》和《海上故事》。《儿女经》拍摄成功并公映。《海上故事》剧本已完成,因导演费穆的突然病逝而夭折。
《儿女经》(编剧署名黄笛)是一部喜剧片,系黄永玉以友人唐人(《金陵春梦》一书作者)的家庭生活为素材而创作。《儿女经》于1953年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公映,大获成功。一位研究香港电影的专家张燕,曾这样谈到《儿女经》的历史影响:“影片《儿女经》是社会写实与伦理主题成功结合的王牌之作,影片在一对夫妇含辛茹苦养育七个孩子的家庭故事中,设计了众多充满生活趣味的精彩细节,以情动人,真实朴素,并细腻传达出社会生存和家庭教育的主题。”
黄永玉在初期的文学创作中,已经表现出对不同的体裁样式和风格的好奇与兴趣。诗歌、散文、剧本;写实性、虚构乃至寓言体的运用……受左翼文艺推动和现代木刻传统的影响,他有意贴近现实,反映香港罢工等社会事件;也受沈从文等前辈文学家的影响,注意艺术克制,追求形式美感,在语言文字与篇章结构上力求凸显个性化风格,并表现出对幽默的天生偏爱。
文学与美术的联姻,也是黄永玉早期创作中值得关注的一大特点。
作为一名艺术家,黄永玉的美术起步与诗人、作家密不可分,其早期的不少木刻作品,均是为诗、小说而创作的配图。进入50年代,黄永玉还为冯雪峰、叶圣陶、严文井、梅溪等人的童话,汪曾祺小说、阿诗玛民间传说、郭沫若诗歌等作品创作大量插图。
在与文学家保持密切交往、与文学作品对应感悟的过程中,黄永玉的文学兴趣和创作欲望也为之丰富与激发。1947年,他发表的《风车,和我的瞌睡》,宛如一首牧歌,风车与水、与田野、与庄稼、与童年乐趣交融,酿就一片甜美与温馨。创作这首诗却非偶然。此时,黄永玉不仅为沈从文的《边城》《吹笛》等小说创作插图,还创作了一组民间情歌的木刻作品,另外还创作了单幅《风车》木刻。这一系列木刻作品,与他的诗有着相同的基调。1950年之后,在香港《大公报》上,黄永玉先后发表《民工和高殿生关系》《猴国之命运》连载,前者为现实报道,后者为政治寓言,均采取图、文并举的形式。发表一些人物特写时,他也喜欢配以人物肖像速写或者木刻作品。这种图文互补的创作特点,在当时文坛上应为特例。
1953年春天,在表叔沈从文等前辈的建议和鼓励下,黄永玉离开旅居6年的香港,携妻子和一岁的儿子,定居北京,并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从此,他全身心投入新生活,以美术教育为职业,以美术为主要创作形式,文学创作则渐行渐远。
在由“尝试”转为“沉寂”的十年时间里,黄永玉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极其有限,总数不超过二十篇,且主要为散文、美术短评。这些作品,尚有一种依然故我的表达习惯。在《森林小学》《森林的黄昏》《两张照片的故事》等散文中,没有多少陈词滥调,也不喜欢用成语之类的表述,而是重在场景、对话的勾勒渲染,文章简约生动而清新。
一时的沉寂,却并不意味着远离文学圈。黄永玉先后为冯雪峰寓言、叶圣陶童话配版画插图,继续保持美术与文学的关联。他又如同当年在上海、香港一样,拥有了一个来往密切、惺惺相惜的文化界群体——从沈从文、萧干、黄苗子、郁风、汪曾祺,到夏衍、臧克家、聂绀弩……唱和、聊天、阅读,文学所需要的种种元素,不经意之间积累于心,渗透于心。
1956年冬天,时值文化界思想活跃的“鸣放”初期,黄永玉以笔名“江纹”,在《文汇报》发表《回来吧,森林!——敬致浅予》。叶浅予是黄永玉儿时的偶像,如他在文章中所说:“我剪过、临过、模仿过他许多的作品。哪怕是一些零星的报头花都很珍惜,一直到现在。”在他眼里,叶浅予曾是一片艺术的森林,但近些年的叶浅予却变了:“……这几年,虽然时常有机会碰见他本人,见他这里那里来去匆匆。但我总觉得这不太像他本人,而是别一个。是叶浅予,而不是画家叶浅予。在这一段时间,他是一位没画画的‘画家’了。唉!‘田园将芜’了。”“从这几幅作品中,我们可发现浅予在艺术上的那种焦虑的创作情绪,就像一个缺奶的乳母,为了孩子,匆忙地从自己的乳房里连血带汗地挤出奶来时的那种焦虑!”
对“焦虑”的这种警醒,或许可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进一步理解黄永玉选择文学沉寂的内在影响——一个人需要不停地创作,但必须建立在从容、节制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地摒弃焦虑。
如以历史眼光审视,一时间的沉寂是黄永玉文学创作的中断,然而,却成了一种意外的拯救。由于沉寂,黄永玉不再需要在香港时期那样,必须以“短、平、快”方式完成指令性创作,避免了陷入演绎政策,配合运动的窠臼;由于沉寂,他不需要像诸多职业文学家那样,不得不为适应新的文学口号、标准,生硬地改变业已形成的创作风格;由于沉寂,他有幸避免了千篇一律的政治语言、以粗鄙化为时髦的社会语言对现代汉语之美的侵蚀与损伤,从而难得地保留了自己源自故乡的鲜活语言,其艺术感觉依然自由而跳跃……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以此来解读黄永玉由“尝试”转为“沉寂”,恐怕再恰当不过了。
03私下写作:“小屋中摸索着未来和明亮的天堂”
黄永玉的“私下写作”,始于1964年。
这一年的春天,黄永玉与中央美院的其他教员一起组成工作队,前往河北邢台地区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在那期间,黄永玉开始“动物短句”的创作。
熟悉黄永玉的人知道,他是一个精力极其旺盛、从来闲不住的人,画画、阅读、聊天……他还有一个习惯,身边总是带着笔,感触一来,随便找一张纸,就写下短句、对联。有时,在与朋友聊天时,忽然会静下来,旁若无人地独自写诗,晚年所写《体系断层》《像文化那样忧伤》《吕荧》等诗,均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的。“动物短句”系列,便是以类似的写作方式,在一个“百无聊赖”的“运动”环境中完成。
选择动物为描写对象,与黄永玉的性情有关。他一直对动物充满兴趣,自小喜欢观察动物,成家了,养狗、养猫,后来甚至养猴子。
“动物短句”,实属黄永玉独创的一种体裁。每个动物只写一句,再配一幅动物画,图文相映成趣,互为补充。
有的短句,如同诗——
萤火虫:一个提灯的遗老,在野地搜寻失落的记忆。
海星:海滩上,一个被扔弃的勋章在呻吟。
燕子:一枚远古的钥匙,开启家家户户情感的大门。
蛇:据说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有一副柔软的身体。
猫:用舌头洗刷自己,自我开始。
蜘蛛:在我的上层建筑上,有许多疏忽者的躯壳。
螃蟹:可也怪!人怎么是直着走的?
沙鳖:看啦!人类的文明在可悲地倒退啊!
猴子:不管我有时多么严肃,人还是叫我猴子。
大雁:欢歌历程的庄严,我们在天上写出“人”这个字。
刺猬:个人主义?那干吗你们不来团结我?
蜗牛:小资产阶级思想?笑话!你懂不懂扛一间房子的趣味?
乌鸦:不过才“哇”了一声,人就说我带来了不幸。
黄永玉是一位艺术家,他更愿意随性情而行,视感觉而动。在这些短句中,讽刺也好,赞誉也好,均可在现实政治语境中找到对应,如个人主义、自我检讨、教条主义、片面性,人性论批判……当时间流逝,政治语境改变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动物短句”在具备“潜在写作”历史价值的同时,仍然有着鲜活的文学感染力,带给人们智慧、幽默的快乐。
正因为“动物短句”具备上述特点,1966年“文革”爆发初期,它们成为黄永玉的一大罪状被揭发出来,并招致批斗。
“动物短句”的转瞬即逝与招致批判,并不意味着黄永玉“私下写作”的终结,相反,在动荡、艰难的日子里,在书信中,在偷偷写下的诗歌中,他一直保持着自己与文学无法割断的联系。
1970年12月,他偷偷完成了历时多日的一首长诗——《老婆,不要哭——寄自农场的情诗》。
《老婆,不要哭》,计二百多行。身在“五七干校”的黄永玉,在经历“文革”初期的批斗之后,下放“干校”劳动虽然艰苦,但也相对少了干扰,反倒获得暂时的喘息。郁积于心的诸般愤懑、不解、无奈,藉以诗怀旧、以诗抒怀,是晦暗生活里的一束心灵之光,再次照亮诗的神圣,照亮文学道路上令人神往的景象——
我看云,
我听城墙上传来的苗人吹出的笛音,
我听黎明时分满城的鸡鸣,
我听日出后远处喧闹的市声,
还有古庙角楼上的风铃。
……
我们的小屋一开始就那么黑暗,
却在小屋中摸索着未来和明亮的天堂,
我们用温暖的舌头舔着哀愁,
我用粗糙的大手紧握你柔弱的手,
战胜了多少无谓的忧伤。
……
中年是满足的季节啊!
让我们欣慰于心灵的朴素和善良,
我吻你,
吻你稚弱的但满是裂痕的手,
吻你静穆而勇敢的心,
吻你的永远的美丽,
因为你,
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
黄永玉喜欢阅读和欣赏19世纪俄罗斯、英国诗人的作品,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到普希金等诗人对他的影响。写作《老婆,不要哭》时,诗人超越于外界纷扰,回到内心的浪漫,营造诗意的纯净。感伤却不悲观,爱情的反复吟唱中,生发出面对苦难的坚毅、自信与乐观。
除此首长诗之外,他同期还创作了另外一首二百多行的叙事长诗《喂鸡谣》。《喂鸡谣》为七言体打油诗体裁,几乎不带政治色彩,不用报章术语,而纯以幽默、调侃风格反映“干校”日常生活,在艰辛的日子里发掘自我调节的喜剧色彩。
从此,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写诗,即便在动荡的日子里——
1974年,黄永玉因一幅“猫头鹰”画,在“黑画事件”中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受到批判后,他回到湖南躲避风雨。在家乡,他先后写作《平江怀人》《一个人在院中散步》等诗,以隐晦表述,写对因“庐山会议”而遭贬黜的彭德怀的怀念,写严峻凄冷下的一种乐观……1976年,北京发生因悼念周恩来而爆发的 “四五事件”,黄永玉曾前去天安门广场,之后,他写下《说是从丰台来的》《老夫妇》《老兵》《哭泣的墙》《邂逅》等,以诗的形式记录历史突发事件,抒发现实忧患。“文革”结束后不久,黄永玉将笔记本上偷偷写下的这些诗歌,挑选若干,交由《诗刊》发表。
黄永玉十余年的“私下写作”,也是一次庄严的、毫无功利目的的文学预演。它预示着,“文革”结束之后,黄永玉将拥有清醒的、雄心勃勃的文学自觉,“大器晚成”的他,收获季节,如期而至。
04自觉与丰收:太阳下的风景
1982年,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大会。获一等奖的诗人十位,老中青三代、九位是人们熟悉的艾青、张志民、李瑛、公刘、流沙河、邵燕祥、胡昭、傅天琳、舒婷,惟有黄永玉一人,来自诗坛之外。
以往,人们只知道他是位画家,而现在,他还是一位诗人。在历时30余年的尝试、沉寂、“潜在写作”之后,他终于拥有了充分的自觉,意识到文学是他干预现实、抒发自我、融入历史的更自由的表达方式与手段。
黄永玉获奖的诗集为《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收录32首诗,一部分属于“潜在写作”时期的作品,其余创作于1979—1982年间。
这是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时刻,浩劫余生的沉痛与兴奋,引发黄永玉文学创作的激情,他以这批诗歌,汇入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潮流。
短诗《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可看作是诗人对“文革”时代特征的高度浓缩:
人们偷偷地诅咒
又暗暗伤心,
躺在凄凉的床上叹息,
也谛听着隔壁的人
在低声哭泣。
一列火车就是一列车不幸
家家户户都为莫明的灾祸担心。
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怨毒的话,
最能唱歌的人却叫不出声音。
传说真理要发誓保密
报纸上的谎言倒变成圣经。
男女老少人人会演戏,
演员们个个没有表情。
此诗足可代表黄永玉的历史态度与批判锋芒。显然,他自己也很看重此诗,故将该诗题作为诗集的书名。
以“现代口语”入诗,正是黄永玉的诗歌艺术特点之一。多年后,诗评家项兆斌仍将黄永玉视为当代诗歌“口语化写作”的最早代表诗人之一,他写道:“《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诗集中的32首口语短诗,均是优美可人的佳作,像对你说贴心话,没有一句是绷着诗人面孔的‘刁钻’‘吊诡’之言,或是文绉绉的诗句。”
同一时期,黄永玉也开始了散文写作。率先完成的长篇散文《太阳下的风景》,写于1979年岁末,标志着黄永玉散文写作一下子就达到很高的起点。
《太阳下的风景》以写表叔沈从文为主,勾勒出大时代里一个小人物的坎坷命运,顽强生命力之中含蕴着浪漫、柔情、忧郁、感伤与悲怆。也是写故乡凤凰城的文化风情、历史变迁,写父母一辈的命运与时代的对应关系,写作者本人的漂泊人生。当他以画家与小说家的综合才能写作这篇散文时,笔下缓缓流淌而出的,恰恰是中国当代散文久违的也颇为缺乏的真挚情感、个性化语言、不拘一格的起承转合,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漫溢诗意的历史感——这正是其散文艺术的魅力所在。
在《太阳下的风景》中,黄永玉这样谈到对沈从文散文的印象:“在1946还是1947年,他有过一篇长文章谈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状,与其说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说是我们乡土知识分子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写照。表面上,这文章犹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实质上,这文章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这无疑也是写作《太阳下的风景》时作者本人的心绪与艺术追求。
自《太阳下的风景》之后,散文一直是黄永玉最为得心应手的写作。散文集《这些忧郁的碎屑》(1994年),《比我老的老头》(2002年),汇集大部分描写人物的作品。如今,《比我老的老头》已发行十万多册,成为备受读者欢迎的著作。
90年代初,黄永玉旅居意大利期间,完成《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书,集游记与人物素描于一体,佐以大量风格各异的插图,文采飞扬,趣味无穷。两年前,这本书翻译成意大利文在意大利出版,成为一大盛事。
杂文也是黄永玉热衷的体裁之一。1985年前后,他在《新观察》杂志以“吴世茫”笔名开设“吴世茫论坛”,以反讽、鞭挞等手法,针砭现实,嬉笑怒骂,一时轰动京城。1989、1990年前后,他在香港《东方日报》等报纸开设“天荒野谭”等个人专栏,发表杂文约三百篇,说古论今,笔锋犀利,为历史留存记忆,为文化提供掌故与见识。
90年代定居香港和旅居意大利期间,黄永玉还开始了他最为看重的文学创作——长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是政治幽默小说《大胖子张老闷外传》,描写1949年开国大典之后的北京文化界以及中南海高层的生活。
黄永玉的文学创作,已经形成了四个鲜明特点:其一,“乡愁”,是贯穿始终、漫溢诗意的永恒主题;其二,“文化的感伤”,是描写前辈文人命运与性格时,最能触动人心的历史感;其三,“幽默”与“机智”,是他人无法模仿的个性特色;其四,“营造汉语之美”,是摆脱了文字的政治性污染,还原语言本色的纯粹、鲜活,贴着土地生长,在空气中自由呼吸的那种优美……
文学行当,伴随黄永玉一生。走进94岁,他还在拥抱着文学自觉。随着《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继续写作,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及其独特贡献,将在当代文坛日益凸现出来,成为一片耀眼的“太阳下的风景”。
作者:李辉 发表于北京系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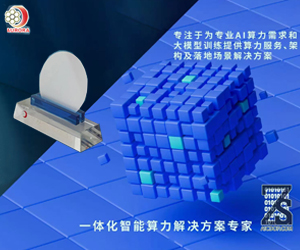




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