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的文明:印度宗教的繁荣与冲突
这一段时间印度在中国的网络上存在感很强,但很多人对印度其实没有多少了解。同为古老的文明古国,印度文化一直保持着其神秘的一面。
古时候的印度盛产宝石、香料,在西方人看来,这就是天堂。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丝毫不掩饰他对印度的赞美,称那是一个黄金遍地的国度。
他的这句话引来了西方的狂人。于是,英国殖民者浩浩荡荡地来了,自十八世纪末开始,英国开始实行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日的到来,印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今年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生后,印度国内民族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但其实此前印度在外界印象里并不是一个国内团结稳固的样板,为什么这次能够做到全国一个声音呢?这就要从印度的宗教和民族政策说开去。
教派繁多,信仰高于一切
印度《宪法》确定,印度是一个世俗国家。不过,印度宗教繁多,堪称“世界宗教博物馆”,只要是世界上有的宗教,印度差不离都有。本土宗教包含印度教、印度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等,外来宗教包含伊斯兰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因此,《宪法》的“世俗”更应理解为:其一,印度不设国教,国家治理以世俗为基础;其二,各宗教平等,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
无信仰者只占印度人口总数的0.05%,也就是说,几乎每个印度人都有他们信仰的宗教——无论是他们本土传承的还是外国带来的。
《西游记》中讲述的唐僧师徒四人到西天取经,其中的西天就是现在的印度。按正常逻辑来说,印度一直标榜自己是佛教起源国(实际起源国应为尼泊尔),印度应该佛教徒很多,但结果恰恰相反。印度绝大多数人信印度教,占印度总人口的80%以上;其次是伊斯兰教信徒,占12%左右;再次是锡克教徒和基督教徒,各占2%左右;佛教徒和耆那教徒分别只占0.8%和0.4%。
在印度,可谓“三步见一神,五步过一庙”。有文献记载,“印度有3.3亿个神灵”——那是印度人口为3.3亿之时的材料,言下之意是每个印度人都拥有一个神灵,因此此数为虚指,形容数量之多。
教徒们的日常生活与宗教和神灵密切相关。以印度教徒为例,对他们来说,宗教信仰高于一切。正因如此,很多在外人看来无法理解的事,对一些印度人来说却再正常不过。比如,为了求雨,印度教徒在神庙里为两只青蛙举行盛大的结婚仪式;为了避免洪涝灾害,又为它们举行盛大的离婚仪式。又如,为避免染上新冠病毒,一些神庙举行焚毁病毒魔像的游行活动;为杀死新冠病毒,一些信徒饮牛尿、在身上涂抹牛粪等。这类活动都是在十分虔诚礼敬的情况下进行的。
印度还有极端贫困的部落地区和城市的棚户区,贫困和不平等仍然困扰着很多印度人民,但其实许多印度人很懒散,没什么事业心,满足于拿一点工资,然后就是吃斋、念佛、做祈祷。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对于印度人来说,外在的东西相对没那么重要。恰似他们信奉的印度教,即便深处在贫穷的环境中,没有任何希望,但是跟随着信仰的方向,终会有灵魂飘荡的远方。
种姓制度影响重大,至今无解
印度教是世界上第三大宗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创始人的宗教。在印度的发展过程中,对社会治理体系影响重大的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不得不提。
种姓的梵文是“varna”,代表“肤色”,后来引申为“所出生的族姓”。公元前14世纪,雅利安人自中亚入侵南亚次大陆,驱逐原住民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是白种人,达罗毗荼人肤色较黑,为了确保其统治和执政权,雅利安人以血统论为基础建立了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将印度人分成4个等级:
第一等级“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以及享受奉献的权利,主教育,负责垄断文化教育和报道农时季节以及宗教话语解释权;
第二等级“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他们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主政军,负责守护婆罗门阶层生生世世;
第三等级“吠舍”是普通雅利安人,政治上没有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主商业;
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由伺候用餐、做饭的高级佣人和工匠组成,是人口最多的种姓,被认为低贱的职业。在种姓制度中,来自不同种姓的父母双方所生下的后代被称为杂种姓。
此外还有被排除在种姓制度之外的贱民“达利特”,他们被视为是“不可接触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种姓等级使许多印度人固化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地洞”的观念。正如印度教的圣经之一《薄伽梵歌》中的一段经文说的:“做你分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分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是死。”
这种观念导致绝大多数印度人往往只在意本种姓的利益,对其他种姓的事务漠不关心,民族内部缺乏凝聚力,并进一步导致印度在面对外来入侵时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力量,因此印度虽然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占领这块土地的统治者却换了一拨又一拨。
20世纪30年代,圣雄甘地提倡提高贱民地位,发动“哈里真”运动。他坚持认为应该把贱民改名为“哈里真”,意思是“上帝所爱的人”。1947年,印度独立后,颁布废除种姓制度的法律。
印度《宪法》第15条规定:“禁止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的歧视,所有公民不因其种姓而在进入和使用商店、餐馆和公共水井等方面受到限制。”印度先后推出一系列法律,旨在减轻种姓制度的负面作用。
但种姓制度虽然在法律上被废除,留在人们传统观念中的“顽疾”却难以消除。信奉轮回的印度教认为若破坏种姓制度,会永世不得超生,故上至婆罗门下至贱民,均不敢废除该教义。因此,直至今日,种姓在社会运作和生活中,仍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由此导致的恶性循环成了一个印度发展过程中近乎无解的难题。
矛盾突出,时刻面临宗教冲突反噬
种类繁多的宗教除了给印度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也使社会中时有宗教冲突,成为印度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其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尤为尖锐,历史上他们之间爆发过无数次流血冲突,死伤人数和毁坏财物之多,已超越巴以冲突,被称为二战以来和平时期最大的悲剧。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很多方面都是互不相容甚至对立的。如两教教徒对于猪和牛的态度正好相反,一边认为牛是神灵,一边特别爱吃牛肉;一个是多神教,一个是单一神教;此外,伊斯兰教宣称“凡穆斯林皆是兄弟”,而印度教有森严的种姓制度。
至于其他的宗教,佛教、耆那教、基督教和印度教之间倒是矛盾还少些。佛教和耆那教本身和印度教非常接近,它们分享同一套世界观,只是采用不同的方法论,所以教义上的碰撞比较少。再有就是他们数量比较少,对印度教不构成太大的威胁。
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恩怨早在13世纪就初露端倪。印度教是印度次大陆本土形成的宗教,伊斯兰教则是外来的宗教。1206年,进入北印度的穆斯林建立德里苏丹王朝并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后,就产生了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关系问题。1526年,外族人巴布尔建立莫卧儿帝国,将伊斯兰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伊斯兰教统治印度长达几个世纪,在此期间,据说毁庙建寺的事儿也干了不少。
大量不甘忍受印度教种姓制度压迫的“不可接触者”皈依伊斯兰教,而印度教高等种姓则因此把伊斯兰教等同于“不可接触者”,视之为不洁净而加以鄙视。还有一些激进的印度教徒认为,伊斯兰教是入侵者的宗教,它在次大陆的繁衍,是印度教的耻辱。
印巴分治时,双方在旁遮普、克什米尔以及孟加拉地区都杀红了眼,据英国人统计死了一百多万。这本就是无解的血海深仇。
印度建国之后,执政的国大党鉴于穆斯林在人口上是少数,在经济上比较弱势,出台了一系列照顾穆斯林的政策,印度的宗教冲突暂时得以缓解。
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大党一党独大地位的终结,人民党等政党为了上台执政,抨击国大党的宗教政策对印度教徒不公平,号召印度教教徒团结起来,为争取平等地位而战斗,并以重建印度教的“罗摩庙”作为政纲的重点之一。
罗摩是印度教的大神,其诞生地——北方邦的阿约提亚曾有一座罗摩庙,1528年,莫卧儿帝国的穆斯林统治者拆毁了罗摩庙并在原址上兴建了巴布里清真寺。历史上印度教徒曾多次要求拆寺建庙,为此双方曾多次发生宗教冲突。
这种从下至上,席卷全印度的宗教狂热最终以毁灭迎来了他的高潮。1992年12月6日,几十万狂热的印度教徒们手持锄头和铁棍,强行闯入并拆除了巴布里清真寺。这一天的宗教冲突,导致约2000人死亡,大部分是为了保卫清真寺殉教的穆斯林。
这件事的影响还不仅是宗教冲突本身,借着煽动情绪,印度人民党终于在4年后的大选中,击败国大党,第一次统治了印度。
人民党的上台,加剧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又被称为”印度教徒主义”)的抬头。印度教徒主义是一种带有强烈教派主义色彩的社会政治思潮,强调印度教至尊,在印度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特别是在2014年大选后,舆论批评纳伦德拉·莫迪带领的印度人民党对党内强硬派的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主义言论不加管束。
例如,2015年,印度人民党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马诺哈尔·拉勒·卡塔尔推动印度教经典文本《薄伽梵歌》纳入国家义务教育。此前不久,南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印度人民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认为,清真寺不是圣地,不像印度教寺庙,因此可以随时安全拆除。
2019年11月,印度高等法院经过漫长的扯皮,终于对巴布里清真寺的归属做出了最终判决:寺庙土地归印度教徒所有,穆斯林在附近得到一片土地重建清真寺。
印度教徒得到了胜利,今年8月,莫迪亲自为罗摩神庙奠基。
印度的穆斯林群体,应该觉得这是重大耻辱。
印度教徒主义的影响正在向社会的方方面面扩展,甚至包括公民的饮食习惯及合法的屠宰和交易活动。在保护圣牛的口号下,印度国家志愿人员服务社(RSS)的纠察队对食用牛肉者、交易活牛者及屠宰场所有者处以私刑,而这种私刑行为不受法律制裁。这使得广大穆斯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有舆论称,印度在莫迪的带领下正在变成“印度教的印度”。
去年12月,莫迪政府推出了《公民身份法案》,规定所有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来到印度的“受宗教迫害的少数派”,如果在印度居留时间超过五年,可申请获得印度公民身份——包括印度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拜火教徒,但唯独排除了穆斯林。这标志着将“宗教平等”写进宪法的印度,破天荒地通过了一部以宗教区别对待公民身份的法律。
莫迪领导下印度人民党影响力快速增长,但似乎在日渐破坏印度世俗传统和宗教多样性。对此,印度有识之士不乏批评之声,但这种声音在逐渐减弱,印度媒体则基本上采取了附和莫迪政府的态度。而印度反对派由于影响下降,也很难对印度人民党及莫迪政府形成制衡。
除了内政,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外交的负面影响也已逐步显现。那些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鼓动和吹嘘起来的民族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冒险主义。频发且不断升级的边境矛盾就是集中表现。
马克思评价印度:“一部印度历史就是一次一次被征服的历史!”通过关注过去的教训,印度或有可能找到解决今天问题的机制。但英籍印度裔作家奈保尔对印度也曾有这样一句评价:没有任何文明那么缺乏抵御能力;没有一个国家会那么轻易地被侵袭和掠夺,而从灾难中学到的又那么少。
文:马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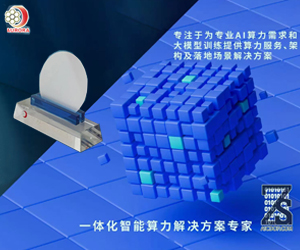




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