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不能缺席新治理
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曾经说过:黄金是蛮荒时代的遗物。话虽如此,黄金在数字货币拥趸者众的现代经济中,依然魅力无穷,在货币体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不过,黄金参与现代经济的方式,已经变了:央行纸币信用奔腾在前,黄金作为过剩流动性的终极归宿,价值储藏地位愈发突出;新旧货币貌似不两立,长存劣币良币之争,其实互相度量,互相补位,达成金融新秩序。
社会秩序的进化,应该是新旧元素和谐共存,良性互动,形成动态的社会新治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如果说有什么全社会参与和推动的新元素、新动力,那非新经济崛起莫属。电商平台实现足不出户任选任购,物联网能够远端控制消费终端和即时监控物流,共享理念催生了扫码骑行和约车出行,手机刷票通勤、面部识别乘坐火车,这些都是新时代的见证。
以“平台化”和“移动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最大特点就是能够远端实现各类信息的数字化收集、标签、传输、匹配和分享,“无接触”地促进生产要素的组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这种经济驱动元素开拓出广阔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也将为我们的社会治理注入新动力,提供新模式。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很多省份启动了高级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采取了强力的居家隔离措施。在家刷社交软件、看流量视频、参与远端会议、接受线上教育,成为疫情期间大家共同的体验。这也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切身感知到的新经济在疫情中发挥的独特作用。遗憾的是,除消费端需求的满足之外,新经济主流元素很大程度上缺席了疫情防控过程中的社会治理。在村口安排大爷持棍棒站岗,在社区门口进出时报口令,半真半假,一时成为社交软件广为推送的笑谈。
新经济元素的缺位
新经济缺席新治理,典型地体现在“三缺少”:
一、缺少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的自动化整合。照理说,航空和铁路部门拥有出行个人的详细出行记录,电信运营商拥有持手机个体的即时位置轨迹、上网行为等多维度信息,这些数据资源理应成为“数字防疫”重要支撑,使得疾控部门及时掌握目标人员流动情况。但是大家看到的现实是,疫情期间,无论是疫区人员流动还是非疫区人员管理,都需要人为设置岗哨和关卡一遍又一遍地筛查,需要网格员一次又一次电话或者登门询问确认。为防止挂一漏万,甚至出现凡持湖北字头身份证不能住酒店、不能购票出行的情况,导致不在疫区或者没有经过疫区的湖北人无法返程正常复工和差旅。
疫情检查站、社区、派出所、交通部门和通信部门都掌握一部分信息,在行政上也能够互相沟通互相配合,但是在处理信息的手段上比较落后,信息无法自动化打通,无法进行及时核对。结果是既存在重复劳动,又存在管理真空,还容易造成不必要的人员聚集和接触,形成传染风险。从管理链条上看,社会基层在忙于应对疫情的同时,还必须对疫情蔓延状况、人员构成和复工进展等情况,层层填写报表,逐级汇总上报,基层人员无奈地称之为“表格抗疫”。这与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重大突发事件后的应急方式没有本质区别。这种以传统经验和机制为基础运行的治理模式也很有效果,但在精准度和效率方面的确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也没有采用新经济催生的科技手段和应用场景,浪费了新经济基础下积累和运营的数据处理能力。
二、缺少公共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建设。2003年非典疫情以后,中央和地方花费巨资建立了“全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也称“网络直报系统”,涵盖法定传染病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系统、专病管理系统、医院死亡病例报告系统、健康危险因素报告系统、疾病预防控制基本信息系统等6个子系统。但是,此次新冠疫情之初的病例以及疾控系统的内部沟通,仍然主要通过口头、邮件、电话的方式;中国疾控中心的两批专家组在到达湖北之前,也未能通过该网络直报系统获得重要基础信息。也就是说,该系统在疫情之初并没有发挥监测作用。当然,这里面有医院辖地管理的汇报路线和机制问题,也有各级医院对系统的认知和使用习惯问题,还存在系统本身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持续更新、各地医院数字化水准参差不齐、系统配套应用机制建设不完善等问题。
数字化在疫情管理中缺位,暴露了国家级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缺少围绕公共卫生资源和健康的大数据应用,无法监测区域医疗资源和卫生状况,难以预测乃至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果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到位,那么从疫情初期开始,相关部门就可以准确掌握湖北省和武汉市有多少个口罩,库存在哪里,每天有多少新增病人,都是什么类型的病人,医生、科室分布状况,床位存量供应总数以及分布等等,就能做到心中有数,调度有方,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医疗物资短缺和医院挤兑现象。
三、缺少公益机构的智能化运作。公益和慈善事业相关财物,由于笔数多,金额小,来源广,对透明度要求高,本应是智能化应用的绝佳舞台。腾讯公益、水滴筹等慈善平台就是典型例子。这次新冠疫情,关注度高,各种捐赠参与面大,是对公益慈善运营能力的一次压力测试。可惜的是,疫区公益慈善机构最终体现出来的处理能力,不但离大家的预期差距很远,甚至无法完成基本使命,在汹涌的舆情中成为众矢之的,再次损害了公共慈善机构的公信力。
很难想象,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今,在新经济勃发的年代,在“双十一”单天成交额达到4101亿元、物流订单12.92亿单、订单创建峰值54.4万笔/秒的系统处理能力基础上,我们却无法及时处理百亿计的捐赠资金和不足1亿件的社会捐赠物资。缺少智能化的公益事业管理和应急资源调配平台,捐赠的物资靠传统方式记账和调配,安排入库和出库,肯定难以快速送达有迫切需求的地方。
马化腾曾经说过:数字化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公益。把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很应景:这个时代的公益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数字化。
传统与现代手段的结合
新冠疫情暴露出来的“三缺少”,说明原有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方式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虽然仍可继续发挥作用,但也表现出不适应新时代的一面。面对大面积紧急社会公共卫生事件,面对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传统的以属地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就表现出能力不足的问题,简单依靠行政手段的管理型治理就会显得力不从心。全球数字经济国家竞争力评价结果与排名,中国的数字产业排名第1,但是数字治理排名25,就说明了数字经济在治理方面的滞后。
要用新经济手段革新社会治理,需要做好如下三点:
一、以制度为中心做好治理数据的基础建设。数据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要素,数据系统即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共生系统。各社会治理职能部门已经架设了基站、摄像头、传感器等技术手段,实施了数据获取,但却没办法合理、高效利用数据,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相关制度。在何种情况下采集数据、采集何种数据、如何应用数据、如何共享数据,这是一个涉及个人隐私和公权力边界的高度敏感话题。解决这个问题,让数据活起来,不能光靠技术手段,还要靠制度体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据本身的确权机制。技术上,给数据加上身份或者时间戳,验证其唯一性,这就具备了使用价值。但是要广泛地体现这种价值,需要如同肖像权、知识产权一样,在制度上给数据界定产权边界。若要交换数据,就需要付出对价。二是数据信息交流和报告,与行政管理流程的制度要匹配,治理的责权利需要有强大的数据权属和信息流支撑。
二、以人为本做好数据的统筹和归集。对比各国防控新冠疫情的措施,中国在及时发现患者生活轨迹、锁定接触者、有效隔离疑似等方面,是优于其他国家实践的。这建基于对人员流动信息的及时和精准掌握。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滥用个人信息,要以人为本,以应急管理为需,善用数据。
目前,电信运营商可获得通讯服务使用者的位置信息,民航、铁路等交通服务机构拥有出行纪录,卫生部门掌握病例和疫情信息。在信息归集基础上,发生重大疫情时,防控部门可监测区域人口流动情况,绘制个体在全国范围内的移动轨迹,确定被感染者的疾病传播路径,定位感染源,再配合关系图谱,锁定密切接触者并采取防控措施,从而降低乃至堵截疫情传播。这种基于人员流动的信息统筹利用方式,在当今全球化图景下,可以成为未来任何传染性疫情防控的基本范式。
三、以共享为思路做好数据的协同共治。数据收集并确权之后,一切数据的交换,都应在依法合规和商业原则下开展,并不必然要求共享。但是,遇有重大社会突发事件,需要进行覆盖面更广的数据交换和验证,共享数据就成为新时代实现高效社会治理的必要手段。社会各子系统的关系协调以及良性互动,有赖于社会治理各主体进行协同,数据共享也需要参与和支持这种协同。各级政府可以与运营商和大数据企业合作,建立集成各种数据信息的大数据平台,以实现对人口迁徙数据、疫情传播的智能分析,做好风险预警和社区管控;通过对人员、电力、交通状况跟踪,确定各区域、各行业的企业复工水准,以评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逐步建立新经济时代的消费习惯、技术范式、数据意识和数据能力。社会治理也应跟上新趋势,应用新模式,更好地结合传统与现代手段,服务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文:胡艳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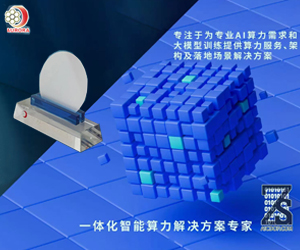




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