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敦煌唐飞天壁画之美
敦煌石窟坐落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榆林洞等共735个石窟,内有历代壁画 4.5万平方米、雕塑两千余尊,可谓是宏大而多彩的佛教艺术圣地。而壁画,更是这宝窟中一朵绮丽耀眼的奇葩。
敦煌石窟的修建时间跨度大,从十六国前秦建元二年直至清代,长达 1400 多年,折射了各朝的历史,也浸染了各代的幻想。而唐代——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全胜时代,更是在敦煌石窟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飘逸的线描笔法,鲜明斑斓的色彩,灵动传神的人物造型,让飞天这一佛教艺术题材中的明珠,在唐朝盛世绽放了新的光芒。
溯源飞天:多元文化孕育的复合形象
中国道教文化中本就有“羽人”形象和飞仙意识,在佛教“天人”传入后,历经中国独特的绘画造型观念的陶冶,中国飞天的面貌逐渐清晰了起来。敦煌壁画中呈现的飞天形象,是印度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共同孕育且长期融合而形成的结晶。飞天周身不长羽毛、背后不长双翅,仅凭罗裙薄纱便可扶摇而上,飘然于云海间,却又不依附于层层云霞,神情泰然自若,一派祥和。
在佛教产生前,古印度就存在着被民众信仰的天神。佛教兴起后,这些神话与其他宗教中的诸神便被重新编排进了佛教教义中,从而产生了须弥山上的七十二“诸天”。而在“诸天”之中,最为常见的便为干达婆和紧那罗。干达婆以香为食,擅长音乐,是为香音神;紧那罗擅长歌舞,是为天歌神。紧那罗有男女两身法相,其中“男则马首人身能歌,女则端正能舞”,常与干达婆形影不离。他们不以酒肉果腹,专采集百花香露,穿梭于云雾与菩提树之间,以歌舞相伴遨游。每当佛陀讲经说法或涅槃之时,他们便凌空飞舞,奏乐散花,这便是早期佛教中的“天人”形象。
而在佛教“天人”形象传入之前,我国就已产生了“羽人”观念的萌芽。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我们的祖先渴望突破肉身束缚,自由地飞天遨游,便发挥想象将人体形态与翅膀、羽毛进行了精妙结合,创造出了“羽人”的形象。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羽人的崇拜有增无减,并将引导升天的功能加诸于羽人,从而演化出了各种神话传说。而道教的兴起则促使“羽人”加快了向“飞仙”的转变。不论是贪恋今世繁华的王公贵族,还是躲避现实困苦的黎民百姓,都愿意相信肉身死后灵魂不灭,以期死后能够得道成仙,飞升至帝乡。于是,人们纷纷在墓穴和祠堂的墙壁上大肆描绘那些身穿红袍、长发飞扬、背生羽翼、腾云驾雾的“羽人”形象,以此寄托“羽化而登仙”的愿望。
佛教在西汉末年经西域传至中原,飞天的形象也随之开启了演变的序幕。从职能方面来讲,佛教飞天与本土羽人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佛教飞天是佛陀的侍从,为弘扬佛法而存在;而羽人是人们与天沟通的媒介,引导灵魂通往升天之路。当佛教传入后,飞天的形象迅速地博得了人们的关注和喜爱,而人们也自然而然地从本土文化观念的角度看待他们,逐渐把羽人的职能转加到了飞天身上,将飞天视作众生与佛陀沟通的桥梁。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当时的许多墓室和祠堂的墙壁上同时出现了羽人和飞天的身影。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构架上已经开始使用线条,但形象上依旧显得概括笼统,神韵上也显得稚拙朴实。到了隋朝,敦煌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飞天也迎来发展契机,有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下,羽人褪去了背后的丰翼,赤膊围裙,系项链于颈间,绕飘带于肩上,飞入了佛教的云霞之中;天人也抛开了健硕的躯体,变得清秀曼妙,摘下了项后的圆光,挽起了发髻,擎上了道冠。魏晋南北朝时期稚拙的飞天形象和隋朝时期交融性的飞天形象,是唐朝飞天样式完全中国化的前奏。
再塑飞天:唐飞天造型的蜕变
在唐朝的统治下,敦煌开凿了二百多个佛窟,成为敦煌石窟艺术最为辉煌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孕育了经济的繁荣与艺术的发展;在与周边国家的频繁往来中,佛教也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僧、道生活得到了皇室的优厚支持,形成一种地位特殊的经济——寺观经济;而海纳百川的开明政策、大胆开放的社会风气更是推动了审美需求的转变,佛教绘画不再仅是为避世游仙寻找寄托,更多的是在歌颂和赞美现实生活;此外,地域文化进一步融合,印度、西域、中原等多种文化的特点被飞天所吸收。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飞天壁画不断革故鼎新。
唐朝敦煌飞天最为突出的转变便是性别由男性转为女性。印度佛教艺术中男女性别特征异常夸张,这种造像形象初传入中国时,就受到了传统伦理道德观的抵制。南北朝时期,菩萨和飞天的形象出现了无性别和女性化的两种不同倾向。即使保留部分男性特征,人物在神情和服饰上也更接近女性。到了唐代,社会风气开放,人们追捧貌美丰艳的艺伎,推动了飞天形象女性化的进程。唐朝画工以仕女图中的形象对飞天进行大胆创新,笔下的飞天面部丰润、双颊绯红、五官清秀,如同王妃贵妇一般穿着华美的丝绸锦缎,身材婀娜、姿态摇曳、顾盼生辉。这些秀美丰腴的飞天形象,使得飞天在宗教的庄严神圣之外增添了浓浓的人情味,拉近了神与人的距离。
在唐朝以前,飞天形象的动态走向多为“U”形、“L”形、“V”形,且肢体比较笨拙单一。而在唐朝时期,画工们不仅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更加具有曲线美的“S”形,还创造出了俯冲、盘旋等动感十足的新姿态。她们或抱着琵琶,或吹奏长箫,或高捧花盘,变幻无穷。“S”形飞天的姿态与唐代舞俑“三道弯”的舞姿非常相似:飞天的腰肢灵活地扭转,使得臀部上翘,单腿或双腿屈膝。飞天的“S”形轮廓是充分调动肢体动作与环绕于周身的飘带来共同构成的,呈现出曲折回环的强烈节奏感。在“S”形轮廓的衬托下,飞天的身形也显得更加修长匀称,曲线美感的展现淋漓尽致。飘带长度被夸张到三倍于身长,或呈弧形,或呈螺旋状,伴随着飞天的舞蹈而旋转起伏,使动态的速度与无形的气韵相得益彰。这也为原本威严肃穆的宗教艺术,带来了动静相宜的调和与平衡。
说到“S”形造型,不得不提的就是唐朝飞天壁画中线条的使用。自中国画诞生以来,线条就是主要的造型手段。不论是战国时期的龙凤人物帛画,还是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线条对物象美感都至关重要。自战国时期开始,线条也成为了飞天的重要造型手段,但较为敦实散漫。到了唐朝,细腻流畅的兰叶描渐渐取而代之。画匠多用替代土红色的朱砂色来勾线,飞天的轮廓立刻显得清晰明快。而在飘带和衣纹等细节上,画工们常用圆转飘逸的笔法细细描绘,极力表现长裙和飘带等丝织物的柔软质地。同时,线条在深浅上也有了干湿浓淡之分,形状上有了粗细曲直的不同,强化了虚实强弱、前后远近的层次变化。唐朝画工还特别注重以线条的提按顿挫、轻重缓急来表现形体结构的转折和变化,使得飞天的造型层次更加丰富,细节更加精致。
与线条相应的,是上色技巧。敦煌壁画的着色手法和配色倾向随着时代变迁而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在魏晋南北朝,壁画主要受西域画风影响,起稿时常选用土红色,完成后用墨线复勾,受西域飞天影响而出现了大面积晕染方法,整体古朴粗狂。到了唐朝,画工们用色更有层次,常用叠晕与渲染达成渐变效果,突出色彩的美感以提高作品的装饰性。红色系等一些明快艳丽的色彩使用广泛,飞天壁画整体变得更加艳丽多彩。在此时期,壁画绘制使用的大多是石性的矿物颜料,使得壁画上的色彩越千年而不变。
初唐时期,壁画大多不涂底色或涂与石窟颜色相近的土黄色,整体色调显得较为温和。盛唐则采用了白色涂满墙壁。在白底色的衬托下,其他色彩显得更加鲜亮明快。在赋色技法上,唐朝飞天壁画常用层层叠加的新技法:在画面内容布局妥当后,先扫染大面积的天空、远山,颜色渐深的区域则用相同的颜色多次叠染;然后选用接近肤色的色彩,根据人物面颊的起伏、躯干四肢的转折进行深入的分染,增添立体感;再对面部身体进行整体平涂,使之融为一体;最后对于衣纹装饰等细节进行深入刻画。对于衣裙飘带,唐朝画工也琢磨出了许多设色技巧:用各种对比色平涂服饰主体,再用同类调和色罩染衣纹;表层以薄色染衣裙,再点缀小花;在重彩衣裙表层轻拂一层薄色来表现轻纱透体的效果。这些不同的赋色手法,使人物造型更加立体丰富,又与环境融洽相合。
唐朝敦煌壁画在继承并发展了传统技法的同时,融合了外来艺术的精华,形成了线条和色彩上既突出主次又彼此交相辉映的画风,创造出了带有中华民族传统情感色彩的飞天形象。在这些飞天形象的身上,罗裙飘带也由简单而程式化趋向世俗化。
装饰飞天:开放而繁荣的世俗服饰文化
初传入中国时,飞天的服饰没有明确的固定样式,而是沿袭并简化了菩萨的造型传统:头戴宝冠、上身赤裸、胸饰项圈、肩披丝帛、下裹长裙等等。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佛陀,而飞天从属于佛陀,处于次要地位,仅作为装饰陪衬的点缀出现。因此,比起倾注心力描绘菩萨的服饰,画工们对飞天的描绘则通常是寥寥数笔。
到了唐朝,经济鼎盛,社会风气开放,戒律的禁锢相对薄弱,女性的穿着也愈发异彩纷呈。唐朝女性服饰以上襦下裙为特色,衣袖变得宽博。唐沿袭了隋末遗风,民间妇女也盛行“宫装”,重视装饰,以争奇斗艳。唐朝还流行坦领,袒露素胸于外成为一时之风尚。且唐朝时期纺织业兴盛,各地生产品类繁多的纺织品,其中的款式裙形、花纹图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壁画的创作。从莫高窟里隋唐的壁画来看,飞天的头顶都梳着发髻,身着秀丽的窄袖长裙。但隋朝和初唐时期均没有发冠和其他装饰,为世俗少女的样式;到了盛唐时期,飞天则戴起了精美华丽的宝冠,曳地的长裙上也印刻着精致的纹饰。这些特征和周昉《簪花仕女图》中体态丰腴、着团花长裙披薄纱的宫廷贵妇如出一辙,尽显雍容华贵的气态,可见现实生活对敦煌壁画内容的影响已经达到了非常深入的地步。这些细致入微的装饰细节淡化了飞天身上宗教的神秘感,让其世俗化特征越来越显著,如同打上了盛唐社会的烙印。
从飞天的具体服饰上来讲,唐朝也改良和创造了新的造型元素。在隋唐时期,飞天的上身装束主要有半裸、僧祗支、袈裟、络腋四种。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譬喻品》云:“尔时四部众,比丘尼,优婆塞,干达婆等天人,见舍利佛于佛前受阿褥多罗三藐菩提记,心中欢喜踊跃无量。各个脱身上所着上衣,以供养佛。”画师们便据此开辟了一个人体艺术的新创作领域。隋代时期出现了着袈裟的飞天形象,飞天多斜披袈裟,袒右臂以方便劳作,右臂腋下缠绕络腋。其中络可译为缠绕,腋可译为腋下,所谓络腋也就是能够包裹并绕过腋下的服装。在早期的敦煌壁画中,身着络腋的飞天形象并没有出现,到了唐代逐渐增多。这一时期的络腋比隋唐早期更加窄长,且从垂感强烈变为面料轻薄飘逸,主色为红色,并加以绣花描金的点缀。络腋与僧祗支在穿着形式上都为袒右肩而遮左肩,但僧祗支还可作为衬衣使用,而络腋比较窄,不能遮挡住胸部,装饰意味更浓。
帔帛,本是妇女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的薄纱,在唐代广泛流行,也成为了飞天造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是它使得飞天的飞翔姿态直观生动。隋唐壁画中的飞天所着帔帛属于仙帔,常缠绕于两臂,在身后形成圆形环状,余下飘带左右对称。隋代的帔帛单色居多且短而细,从唐代开始,帔帛的种类逐渐丰富,长度变为原先的二至三倍,以红绿色正反双色为主,缠绕双臂后形成双圆环或方形圆环,帔帛的两端也与云彩形成了环绕式的连接。飘带两端成波浪形弯曲缠绕,充满了动感。而那些没有飞起来的舞者和伎乐者,在帔帛的缠绕方式上与飞天十分相似。由此可推断,飞天身上帔帛的缠绕方式正是来源于民间舞伎和乐伎们的装扮。
从下半身来看,唐朝时期的敦煌飞天着长裙和腰裙。早期飞天身着的长裙面料都偏厚,到了隋唐时期,裙长逐渐加长,且从罗裙的摆动和褶皱上能够看出裙下身姿的改变,可见面料较为轻薄贴身。盛唐时期,裙长掩足,宽度增肥,并开始出现当时盛行的团花图案。除了长裙以外,唐朝壁画中飞天的腰腹部位通常裹有腰裙,即一条长方形的布。只着一件腰裙时,腰裙大多长至臀部,若着两件腰裙时,其中一件长至膝部。腰裙面料同长裙,轻薄柔软。这一时期的腰裙有不同穿着方式:有的是将一条长方形裙片围于胯部,两端于身前或体侧系做蝴蝶结状,余下的飘带随身体自由飘动;有的飘带则是系于腰裙内,并由内而外翻出,外加宝珠等作为装饰物;穿两件腰裙时,以内外长短不一的方式穿着,内层较长至膝盖。唐朝时期的飞天裙装以长裙搭配腰裙的方式呈现,增添了层次感。飘带不仅能固定裙装,更是起到了装饰点缀的效果,代替了早期短而直的飘带,渐渐加长。盛唐时期飘带的长度远远超过了裙长,与帔帛互相映衬,化入彩云之间,华丽而飘渺。
欣赏飞天:横相融,纵相承
唐朝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多元文化冲撞与融合的结果,也是反映唐朝社会繁荣和精神世界丰富充裕的一面镜子,更是包容而灿烂的中国传统艺术的结晶。飞天并非孤立的沙漠玫瑰,而是与其他中国艺术形式血脉相融。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后对敦煌石窟进行全面的维护和研究,我国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逐渐系统化。1984年,在原敦煌文物研究所基础上扩建成立了敦煌研究院,更进一步促进了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发展。许多斑驳的作品经过几代学者临摹复原,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历经沧桑却仍旧鲜活。当今的艺术家们在创作时,也可以如精于创新的唐朝画工一样,从飞天中提取生命基因,打磨出新颖独特、飘逸灵动的作品,令飞天的魅力历久弥新,滋养一代代对艺术怀以热诚之心的创作者们。
作者:陈宇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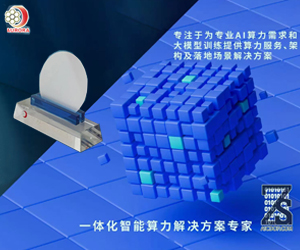




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