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赫德,大清国的洋掌柜
坐落于北京东长安街边上的中国海关博物馆,紧邻海关总署。馆内展示了从周朝关津制度直至现代海关的历史。而当中最有价值的近代海关史部分,几乎相当于一部赫德列传。
从1861年到1911年,罗伯特•赫德(Robert•Hart),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整整半个世纪,除了构建起了一整套完整的现代海关管理制度和队伍外,在那个欧风东来、新旧更迭的特殊时代,赫德还帮助中国开启了现代邮政、港航、气象观测、卫生检疫、商标注册、外语教育、国际展会等事业。中国第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第一个外交使团斌椿使团、第一次参加国际博览会、第一批新式灯塔、第一张邮票大龙邮票,乃至第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西洋乐队等,都与赫德息息相关。
1854年,这位19岁北爱尔兰少年,远离故国,来到遥远的东方。或许他自己也不曾想到,毕生的荣耀和辉煌,都将在这片龙旗飘扬的陌生土地上造就。不过,就像他后来在日记里表述的那样,赫德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与功利:“在中国,自从我踏入了政治生活之后,我的目标总是要做官,只要吸引我,不管是哪个部门。”
从总税务司到太子太保
为了将来入朝做官,赫德先期在香港刻苦学习中文和粤语。等到英法联军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占领广州,亟需懂中文的“干部”,赫德成为求之不得的人才,很快成为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翻译。不久,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清政府聘请英国人帮办海关事务,赫德又一次抢站了“风口”,好风凭借力,青云直上,前往上海,进入海关系统,前期代理李泰国的职务,1863年正式接任总税务司,登上了金字塔尖,时年仅29岁。
赫德在1865年5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看到我所提议全都有了开端,我要努力提出自己的意见;始终留心,一遇有机会便加利用,时间和耐心将使我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与此同时,我必须努力,为著更加重要的工作做好准备,这些工作可能为我打开任何成功的大门。”
这一年6月,赫德将总税务司署从上海迁到北京,从此开始了在北京长达40多年的生活。其目的除了更好地与清政府的各个部院衙门打交道,处理海关税务事宜,同时也是为了更多地介入内政外交问题。
搬到北京不久,赫德就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了他撰写的《局外旁观论》,建议清政府仿效西方变法自强,这成为洋务运动的一份重要文献。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䜣不止夸奖他“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更曾亲密地说“咱们赫德”。而属官们则以“赫大人”相称。
赫德是一位罕见的“中国通”。他承袭了利玛窦、汤若望潜心钻研中华文化的传统,谙熟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熟知官场礼仪,不仅能说流利的北京话,还通晓粤语和宁波方言,因此获得了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与接纳。
赫德为儿子爱德格•布鲁斯•赫德起汉名“赫承先”,直接以“赫”为姓了。赫德甚至教儿子学习八股文,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惜未获清廷许可。否则,历史上还可能诞生一个西洋举人乃至进士。
更为重要的是,赫德兼备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才干。在赫德的掌控下,海关成了一个系统完整、层级森严、高度集中的独立王国,成了大清帝国的“国中之国”,赫德就是其中的王者。当时海关的效率和成就也令人叹服。赫德一方面为海关员工设计了丰厚的薪俸待遇体系,高薪养廉,另一方面严肃纪律,大力打击贪污。在其担任总税务司的近半个世纪内,海关的贪污腐败案件不超过5起。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简直是一个神话。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就评价认为:“赫德对清政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组织的高效率的海关服务工作。” 在赫德的打理下,清朝海关税银高速增长。1861年赫德接手时为496万两,占财政收入的9%。到了1894年,已达2290万两白银,占财政总收入总份额的四分之一。而到1911年赫德去世时,更是达到3500万两。赫德也成了大清国名副其实的“财神爷”。
赫德广泛介入清政府的其他政务。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是由赫德推荐的;聘请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担任清政府的出使大臣,也是赫德支持的;为北洋水师打下基础的8艘军舰,也是赫德动用海关税银从英国订购的;赫德甚至在担任总税务司、总邮政司之后,还提出要求兼任总海防司,不过因薛福成等官员的激烈反对而作罢。
赫德作为总理衙门的顾问,曾参与清政府的外交谈判,甚至直接作为代表与西方列强商议条约草案。他参与签订的条约有《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辛丑合约》等。《辛丑合约》最终的条约文本包括赔款数字,都是参考了赫德的意见建议。
1901年《辛丑合约》签订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自逃难的西安启行回京。为了表彰赫德的功绩,慈禧特意下了一道懿旨:“宗人府府丞盛宣怀赞襄和议,保护东南地方;总税务司赫德随同商办和约,颇资赞助。盛宣怀、赫德均赏加太子少保衔,以示奖励。”回京后,慈禧还于1902年元宵节次日,接见了赫德。赫德在日记里,不无得意地写道:“这老妇人用一种甜蜜的女性声音,非常殷勤地恭维我。”真正的天朝臣子,私底下是断不敢如此大不敬的。甚至赫德1911年死于英国白金汉郡,清政府还按照一品大员的规格,遥授其为太子太保。较之太子少保更晋一级。
见证沧桑的“赫德路”
香港、上海、北京,三座城市留下了赫德在中国的三个主要“足印”。如今世界上以汉字“赫德”命名的道路,只剩下了香港尖沙咀的赫德道(Hart Avenue)。1909年此路以“赫德”命名时,赫德已返回英国故土半年多,但依然挂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头衔直至1911年去世,实际事务由其妻弟裴式楷(Robert Edward Bredon)留在中国代为处理。上海的赫德路(Hart Road),在汪伪时代被更名为常德路,张爱玲就曾住在该路上的爱登公寓。
而赫德生活了大半生的北京,除了海关博物馆中的纪录之外,赫德的足迹几乎已在历史尘烟中消失殆尽。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古都,也曾有一条赫德路。
一个暮春的午后,笔者在北京台基厂头条胡同西口的砖墙上,找到了那块约45厘米乘18厘米见方的灰砖,上面用大写法文雕刻着“RUE HART”(赫德路)。在清末,这一片属于东交民巷使馆区。海关总税务司及办事处都在附近,还曾有一条折角拐弯的海关胡同。后来东西横向贯通了几条新胡同,最北端的便以赫德命名。之所以用法文,大概是因为路南就是法国兵营的关系吧。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这块灰砖曾经尘封在一块锈蚀的铁板之下,四角用钉子钉牢,并与砖墙一起被喷成灰色。直到文革之后某一天,铁板被取下,七个洋文字母重见天日。如今已经无从查考,究竟是谁钉铁板保护住了这块灰砖。我猜想,一定是某位熟知个中历史价值的人士,用这种方式为后人留住了一段记忆。否则,在曾经那场狂狺的文化浩劫中,这种“帝修反”的标识,很难逃脱被砸烂铲除的命运。旁边的台基厂大街,就曾被改名“永革路”。
如今的台基厂头条胡同,主要是商务部及外交部所属单位用房,在性质上倒是仍与海关相近,行人稀少。遥想一百多年前赫德官邸的车水马龙,不禁感叹物是人非。就是在此处,赫德招揽了十几位贫苦的中国青年,用小号、中音号、长号、大小鼓等组成了第一支西洋乐队。每逢官邸内举办宴饮,这些将长辫子盘在头顶的青年,就站在草坪上奏乐助兴。
一百多年来,关于赫德,毁誉参半。民国官修的《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赫德传”,当中评价颇高,“赫德久总税务,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号曰‘客卿’,皆能不负所事。”“受官职,易冠服。”“官中国垂五十年,颇与士大夫往还。”“食其禄者忠其事,实有足多。”
1949年以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赫德被塑造刻画成了一个狼子野心、口蜜腹剑的帝国主义者,甚至比明刀明枪的坚船利炮还要阴险狡诈。但随着时光流转,对赫德的评价趋于公允。如今中国海关博物馆对赫德事蹟浓墨重彩的呈现,即是明证。赫德固然有某些私心考虑,在一些外交活动中偏袒英国利益。但其作为一名客卿和职业经理人,对中国近代化所作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或者说,他做到了在那个位置上,一个外国人所能做到的最好程度。
赫德是一位富有战略眼光的智者。早在1901年,他曾预言:“五十年后,中国将是一个独立的强国,中国人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判断是何等的有先见之明。
赫德仿效中国士人,为自己取字“鹭宾”,既是其名字Robert的谐音,又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宾”表示了其外来客卿的身份,而“鹭”是一种高洁之鸟,古人以“鹭序”形容百官朝觐井然有序,“鹭涛”则形容白浪翻滚的波涛。清朝六品官员补服图案即是鹭。当然,1889年,50岁的赫德被清政府赐予最高阶的正一品,可以穿仙鹤补服。“鹭宾”二字,可谓是远渡重洋、建功异国的赫德,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终极哲学命题的高度概括回答。
1908年,73岁的赫德已经在中国生活了54年,决定回国休养。昔日来华时的青葱少年,此时已是古稀老者。他在总税务司办公桌上钉了一张便条,上写:“1908年4月13日上午7时,罗伯特•赫德走了。”
在正阳门车站,赫德步履蹒跚地登上火车,向前来送行的中外人士挥手道别。赫德亲自组建的那支西洋乐队,演奏了终结曲《友谊地久天长》,为赫德与中国的永别,画上了休止符。
作者:马浩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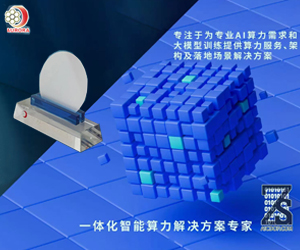




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