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趣味”
“中国趣味”(Chinoiserie)是指17和18世纪在欧洲的室内装饰、家具、陶瓷、纺织品、园林设计方面所表现出的对中国风格的奇异的欧洲化理解,它的出现成为促进巴洛克风格(Baroque)向罗可可风格(Rococo)转变的一个因素,而罗可可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和生活模式,又成为知识界以外的欧洲民众看待和理解中国时所戴的有色眼镜。中国趣味的形成得益于中国商品大量进入欧洲,以及耶稣会士、旅行家们对中国文化的反复介绍。
中国趣味与中国的伦理、政治、儒学、历史、文字等等相比,是非常抽象的东西,归结起来反映了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异国情调的追求,而其直接灵感就来自那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瓷器、漆器、织物、壁纸。这些东西的造型和绘饰的图案无不令欧洲人耳目一新。所以有人指出,尽管欧洲的中国风在18世纪中期才达到颠峰,但它早在16世纪葡萄牙商人开始将瓷器等中国艺术品运销欧洲时就开始酝酿了。这一时期有大量各式各样的中国特产来到欧洲,令人眼花缭乱,忍不住竞相获取。中国商品像是撞开了蒙在欧洲人艺术和审美之眼上的一层雾障,像是为欧洲人指引出生活的快乐之门,因此而大受欢迎。17世纪末的一位作家曾在《世界报》(World)上说,中国壁纸在豪宅中极为流行,这些房子里挂满最华丽的中国和印度纸,上面满绘著成千个根本不存在的,想像出来的人物、鸟兽、鱼虫的形象。18世纪初,中国丝绸也已在英国蔚为风尚,公众审美观由东印度公司的进口商品所指导,连当时的安妮女王也喜欢穿着中国丝绸和棉布露面。17世纪末期,英国东印度公司运来的一船又一船瓷器刺激了英国和欧洲市场对这类商品的需求,英国上流社会以收集和展示瓷器相标榜。类似的风气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同样盛行,路易十四也热衷于通过东印度公司获取大量正宗的中国漆器和其他物品,他一生都对中国艺术品及其欧洲仿制品兴趣盎然,十八世纪中国风尚在法国的流行,就受到17世纪末期路易十四宫廷习气的促动牵引。
进口中国商品俘获了欧洲顾客的人心,本地的生产者和经销商自然不甘寂寞。出于产品竞争的考虑或借助时尚获利的目的,开始摹仿这些中国的橱柜、瓷器、绣品上的装饰风格,这便产生了中国趣味。大体而言,较早大量使用这些中国器物的欧洲国家也较早开始出现中国趣味,17世纪前几十年先是英国和意大利的工匠摹仿中国风格,然后其他国家的工匠纷纷效尤。先是工艺品和日常用品等小物件的仿制,如制造瓷器、丝绸、壁纸;进而是室内装饰与园林设计这些大工程,诞生了风靡一时的“英华园林”并在今天都留下许多建筑痕迹。最早出现的内部装饰主要为中国风格的建筑,是1670-1671年间为凡尔赛王宫而建的特里亚农瓷宫(Trianon de porcelaine),尽管它只存在了17年就被拆除,它却标志了后来席卷法国又蔓延全欧洲的崇尚异国情调的风习。特里亚农宫建成之后,此风迅速扩散,在德国尤甚,其宫室无不有中国屋,且一如特里亚农宫建造的初衷,这些中国屋也都是为王室的女主人而建。
1753年7月24日,瑞典王后收到国王赠送的一件特殊生日礼物,即一座建于德罗特宁霍勒姆(Drottningholm)的木结构的中国亭,她描述道:“我吃惊地突然看到一个真正的神话世界……。”一个近卫兵穿着中国服装,陛下的两位侍从武官则扮成满清武官的样子。近卫兵表演中国兵操。我的长子穿得像个中国王子一样在亭子入口处恭候,随侍的王室侍从则扮成中国文官的模样。……如果说亭外出人意料,亭内也并不少让人惊奇。……里面有一个以令人赏心悦目的印度风格装饰成的大房间,四角各有一只大瓷花瓶。其他小房间里则是旧式日本漆柜和铺着印度布的沙发,品味皆上乘。有一间墙上悬挂、床上铺盖印度布的卧室,墙上还装饰著美妙的瓷器、宝塔、花瓶和禽鸟图案。日本旧漆柜的一个抽屉里装满各种古董,其中也有中国绣品。厢廊陈设桌子:其一摆放一套精美的德累斯顿瓷器,另一张则摆放一套中国瓷器。欣赏过所有东西之后,国王陛下下令演出一场配土耳其音乐(janitcher music)的“中国芭蕾”(所谓土耳其音乐,乃指土耳其近卫步兵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演奏的军乐)。
这座所谓中国亭在建筑上到底有几分中国风味不得而知,但显然它就如17世纪末期流行起的中国屋一样,以内中陈设有关中国的物品而得名。显然,在瑞典这座中国亭里,各种异国情调和欧洲风味混为一体,不仅是物质上的,行为上亦然,中国文武官员和皇子的装扮、中国兵操、中国芭蕾舞究竟什么模样?不过是欧洲人凭借一些来自东方的描述和图形,再参照欧洲人形象和想像力而幻化出的中国人物形象。而这一切由欧洲人创造的活的和死的装饰就成为中国趣味,也成为他们所理解的中国的实体形象。
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为了使中国商品更符合本地需求,早早就开始采用给中国工匠提供加工图样的方法,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末就知道让中国的工匠加工一些具有欧洲风格图案的瓷器迎合欧洲顾客,而英国公司将家具模型运到中国制成漆器的做法在18世纪初期达到顶峰。这样便形成了中国趣味的另一个制造地。质而言之,这些带有中国人艺术观感和手法的欧式图案,与那些在欧洲产生的烙刻欧洲风味的所谓中国图案,都是为迎合欧洲人的口味而诞生的,都是文化混合和变异的结果,对欧洲人而言都是异国情调和这个时代生活理想的表达,并且是通过一种变异和夸张的中国图像来表达。比如18世纪中期进口到欧洲的中国玻璃画,常见的主题是富裕的中国男女在树荫下悠闲舒适地生活,或者中国仕女带着贵族式的无所事事的忧郁神情坐在花园或牧野中,这都是专门设计来吸引欧洲买主的。这不难理解,当时的欧洲,英国已经产生大批富裕悠闲的中产阶级,法国那些被剥夺了政治特权而依然经济富有的贵族们则靡集在宫廷,百无聊赖地以虚耗光阴为最高追求。这些中国画实则正迎合了欧洲上流社会的追求。
在中国加工的瓷器有很多也同样增加了具有欧洲式快乐情调的装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乾隆年间纹章瓷的装饰变化。1735-1753年间以素净的葡萄藤或花蔓装饰最多,1750-1770年间则是显著的罗可可式装饰,1770-1785年间转而为缠绕葡萄藤的黑桃形盾牌,1785年之后黑桃盾牌开始嵌入蓝黑边线和金星,1795-1810年间则变成由深蓝色菱形花纹围成的圈。1765-1820年间欧洲市场上有大量中西参半的由菱形、符号、花朵和蝴蝶构成图案的瓷器。中国进口瓷器在形制上亦做成符合欧洲人需要,比如英国公司订购的便以英国银器为模型,而此风以雍乾时期最盛。如此一来,欧洲人看到的究竟是中国瓷器还是欧式器皿,是中国人的生活风貌还是欧洲有产阶级的人生理想?但恐怕他们都自以为从这些图形、纹饰、质地、形状中所看到的就是中国。
中国趣味不仅仅是由有形物品激发而成,也受到耶稣会士文学和游记作品中相关叙述的影响,它可以说是这个时代关于中国的整体理想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尤其适用于对中国园林的认识。随着耶稣会士所极力推崇的中国古代儒学成为一些启蒙思想家的灵感之源,包含于这种哲学中的造园思想和由此产生的装饰艺术也相应成为当时欧洲一些艺术作品的模型。启蒙时代的欧洲知识界所广为称道的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正是新的园林艺术成长的沃土。17世纪和18世纪前半叶,欧洲出现的一些对中国园林的评论助长了模仿东方的氛围,而这一氛围直接刺激了“貌似图画”(picturesque)园林景致的成长。17世纪中期以来不断涌现的耶稣会士书信和书籍已经在欧洲培养起一片关注中国的土壤,滑落在这片土壤中的任何有关中国的种子要生根、发芽和成长都并非难事。从利玛窦的札记中出现对中国园林的评价开始,姑且不论耶稣会士们对中国园林的揄扬态度,毕竟他们总不忘提到。利玛窦评价了南京的瞻园,提到花园里一座色彩斑斓未经雕琢的大理石假山,假山里面开凿了一个供避暑之用的山洞,内中接待室、大厅、台阶、鱼池、树木等一应俱全,洞穴设计得像座迷宫。(《利玛窦中国札记》)几十年后,葡萄牙著名传教士曾德昭于1613-1636年间在华长达23年,他在归国途中写成的《大中国志》,再次唤起人们对中国园林的印象,他说中国人喜欢在庭院和小径上植花种草,在园中堆假山、养金鱼和各种珍禽美兽,圆形、方形、八角形的宝塔造型美观,有弯梯或直梯,外侧有栏杆。奥地利耶稣会教士白乃心(1623-1680年)也描述过中国人的花园,说它们绿意盎然、令人愉快,因为很方便从河中汲水来浇灌。
对17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最重要的描述来自荷兰使团总管尼霍夫(Jan Nieuhoff)的作品《荷使初访中国记》。尼霍夫的行纪不仅多处提到中国园林景致,而且总是赞不绝口。比如赣州附近某镇的几座自然逼真的大假山,泰和城外的拱桥,南昌一座道观的盘龙柱,湖口城北的假山及旁边的精美宝塔。他对宝塔似乎格外感兴趣,说安徽境内繁昌有一座宝塔,有尖尖的塔顶和陡陡的塔檐,很有意思。清江浦、宿迁、故城、青县都有引起他注意的、或美丽壮观或式样古朴的宝塔。南京报恩寺的琉璃塔虽然已毁,但尼霍夫还是绘声绘色地描述它有九层一百八十四个阶梯,里外有漂亮的塔廊,琉璃生辉,塔檐的檐角所挂铜铃随风奏乐。北京的御花园被他称为是从未见过的漂亮地方,因为里面满是悉心栽培的果树和精心建造的房屋。图文并茂的尼霍夫著作问世之后就如同当年的《马可波罗游记》那般风行,可想而知它对欧洲民众之中国观感的影响力。其实尼霍夫的原文介绍十分简单,然而世面上的各种版本都并非尼霍夫原书,是经编者多方润色的版本,其中对中国风物的描述想来远比上文所引述的生动详细,而这些生动的描述无疑包含了大量从未到过中国的欧洲人的想像。可是,正是这些想像大于真实、道听途说来的信息才是点燃欧洲那些园林爱好者们想像之光的火炬。夸饰之辞助长了那些据说存在于中国的非凡建造物的魅力,而大家又都没去过中国,想驳斥那些迷人的叙述也无凭无据,又逢17世纪末的人们开始厌烦那种中规中矩的法国园林,正需要有个释放想像、创造自由空间的借口。
作者张国刚 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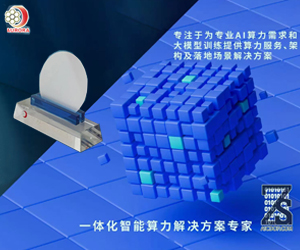




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