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扇之中国扇文化
扇子,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不会陌生。除了在夏日炎炎中借其扇风消暑以外,扇子作为一个文化载体,总会变幻无穷地出现在生活的各个角落,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我们的见闻之中。不论是“轻罗小扇扑流萤”中那小巧灵秀的绫罗团扇,还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中那潇洒挥斥的鸟羽扇,扇子早已超越其形体与设计本意,成为展示执扇者内心的窗户,成为体现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文化符号。
在众多形态各异的扇子中,自古以来最令文人墨客爱不释手的,非折扇莫属。明代文学家杨循吉便曾为它作《折扇赋》,夸赞其“于时则有祛灾雅制,却暑芳姿,昔日之班姬所咏,往年之逸少曾持,敛之不盈于把,圆也有中乎规,出袂而轻飏自动,拂膺而凉思允宜”。而折扇从单纯扇风纳凉的工具,变为沉淀著文化底蕴的雅物的过程,还需抽丝剥茧,从头说起。
根•“扇子送凉,不意成艺”
中国使用扇子的历史渊源远不可追溯,黄帝、舜禹的时代就有扇子的行踪。
而折扇又名折叠扇、聚头扇,据史料记载,它最早在宋朝出现,是由日本传入的。中国的团扇在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后,日本匠人发挥巧思将其缩小,摇身一变成为了“倭扇”,随着商队返回了中国。苏辙在《杨主簿日本扇》中有“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之句,便可佐证。
折扇的原理,却与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伞盖有关。古代官员乘坐的轺车与轩车上,装有形如大伞的“扇汗”,用以遮光蔽雨。这种伞盖的伞骨在伞柄顶端成放射状均匀排列,车马移动时,车中产生的气流便推动伞骨旋转成风。折扇扇骨的排列堆叠与这种设计是密不可分的。
折扇传入中国后,在当时还是“稀得之物”,悄悄流通于底层百姓之间,而受宫廷官绅讥笑,被贬为“仆隶所执”之物。折扇小巧浓缩的特点,也被认为是因“取其便于袖藏,以避尊贵者”。到了元朝后期,木刻《西厢记》插图中的张三也在把玩折扇,印证了折扇的兴起。而在明代,折扇成为日本向中国出口货物的大宗才广为流传,受到人们的喜欢,以至于入明的日本僧人可以用一把日本折扇换得《翰墨全书》一部。
从南宋起,中国艺人便学习日本制作折扇的技艺,尝试生产折扇,所产折扇多为平民所用,较为粗犷。而做工精致考究,能被贵族持于手中的折叠扇则尚未推广,十分罕见。明代后,折扇流传开了,据《在园杂志》记载:“成祖喜其舒卷之便,命工匠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天下”。同时,折叠扇的样式也从“不过竹骨,茧薄纸而已”的简易寒酸,变得工艺繁缛、用料奢华,样式也不断地改头换面。
随着明代宫廷风气的推动,且因折扇本身舒展自如的特点,文人雅士看到了挥洒翰墨的新天地,用妙笔丹青为折扇添加了雅致的色彩,推动其材质和工艺更上一层楼。撒金、雕刻、髹漆等技艺纷纷出现,川蜀和苏州成为著名的折扇产地。从此,执扇成为一种社交礼仪,名流纷纷以此显示自己的儒雅风流。扇子逐渐超脱了纳凉的作用,正可谓“但识扇中趣,何劳扇底风”。
骨•“叠波龙骨,聚风鸾翅”
人们第一眼打量展开的折扇,往往会被扇面上的书画所吸引。但若凑近细细观赏,便会发现精致的扇骨和扇面交相辉映,如同乌枝绿叶上开出灿烂的花朵。俗话说,美人在骨不在皮。对于折扇来说,拥有一副舒卷流畅、材质考究、样式精致的骨架,就等于女子拥有了走向圆润的骨像,不论皮肉是添色还是减分,都已有了几分底色,正所谓“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
扇骨又称扇股,以数目称档,跨度很大,其中以十六档最为常见。因为这样的扇子打开以后呈140度扇形,最宜排布画面。而扇骨的材质,从刚刚诞生时的普通竹子,到盛行之后引入的象牙、玳瑁、檀香、紫檀等,或如士人手持之笏,或为灵兽之甲,或如青龙扶南,或有天香盈秀,色泽质感各异,都有其追捧者。但扇骨最终却“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秀雅物”。同为竹子,不同品种却也有着不同个性:油竹浑厚凝重,紫竹普陀生风;棕竹如项上云锦,玉竹似水磨玉筠;梅箓竹间繁花盛放,湘妃竹上泪迹斑斑;凤眼竹上眠眼迷离,佛肚竹如仙翁捧腹……竹子的材质如人之天性,为折扇的最终面貌打下了底色。之后的扇骨雕刻及扇面上的作画泼墨,都要顺应竹骨的个性,才能显得浑然天成,避免人工巧饰的刻意之感。
不加修饰的素骨方便了人们观赏竹骨的天然肌理和纹路,及其自然优美的形态。但随着工艺发展,竹骨制作诞生了种种装饰技术,如罗甸、雕漆、洒金、嵌螺钿、凤梨漆等,甚至有镂空边骨内藏极小牙牌或通以异香的。扇骨的雕刻与装饰,不仅是为了加工竹骨,更是为了与扇面上的书画鼎足而立,使折扇成为一件贯通而完整的艺术品,扩充其欣赏角度,提高其欣赏价值。
随着技艺的精进,匠人们翻手在这细细窄窄的竹骨上,变幻出种种奇态,折扇的造型便从原始的方头倒梯形,发展出了螳螂腿形、波浪形、蒲叶形等变体,扇头的形状也或为一点梅花、或似藤上的葫芦,再坠以丝穗或玉佩,实为精巧之至。
肉•“鸦青纸,金笺面”
骨既已铸,接下来就要赋予折扇以肉身,承载扇面诗画之美。
扇面以材质来分,有纸面扇和绢面扇之分。素面并不意味着白纸一张,可辅之以染色、发笺、仿古、洒金等工艺,即使画尚未添一笔,也有着细致的纹理和亮眼的点缀,透露著纸张的幽香气息。苏州“舒莲记扇庄”在挖掘古人制扇工艺的基础上,开发制作了清明笺、日月金笺、梅花金、大赤金、镜面笺等传统扇面,观赏与收藏价值兼具。
素面统称矾面,因其平整牢韧、易于运笔、质感素洁而为大众称善。制作素面极其考验纸张,表层选择薄净皮宣纸,中间衬纸要用皮棉纸和连史纸。仔细刮去瑕疵后,将这样的三四层纸裱糊,每隔一段便为扇骨留下余地,以无浆小纸条隔开两侧,并印上店家名号,裱制成扇面。最后,利用扇形模型将扇纸折成扇页,再将扇面两头切齐,通开穿扇骨的隔条,并用丝织品在扇面的边缘沿上一层边,一面扇才算制作完成。
折扇开合的特点要求扇面柔软,摇扇生风的功能需要扇面挺括,这就使得一幅优质的扇面必须刚柔并济,这点正与折扇本身的气质相应和。可见折扇的风雅,是从内而外时刻贯穿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着它的与众不同。
皮•“书说前辞纸面观,画中美人对稍眉”
有了一把优美完整的素扇,岂能不乘兴为它舞墨丹青?
扇与书画结缘具体始于何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泛而观之,在扇面和书画之间,有一个以“扇面之皮”为中心,发展到以“书画之魂”为中心的演变过程。前者以扇面为主体,书画被动适应扇面的形制,仅作为装饰艺术。后者则以书画为主体,书画主动运用扇面这一形式来展现自己,扇面为书画肆意发挥的舞台。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杨修为曹操画扇,误点为蝇;还有“桓温尝请画扇,误落笔,因就成鸟驳牛,极妙绝。又书《驳牛赋》于扇上,此扇义熙中犹在。”是已知的第一个书画合璧的扇面;另有记载南朝遽道湣、章继伯“并善寺壁,兼长画扇”;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川。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辩千寻之峻。”宋代以前,不乏有名人为扇面作书画,但是根据出土的实物来看,它们多属纯工艺性质,有的还很古板、单调,缺乏艺术性。
宋代后书画艺术繁荣,扇面书画也正式开启了侧重于“书画之魂”的格局。其时的作品多沾染了自然、活泼、清新的气息,逐渐从扇子形制中脱离出来。《宋人画册》中百幅小品,题材丰富,刻画细腻,千姿百态。
团扇画与长轴大卷相比,如同从圆窗中窥视另一边的景象,在无形中牵引著观者的目光。与之相比,展开的折扇显然是更为广阔的舞台。扇形的外观使得折扇书画在构图章法和视觉平衡的处理上就显出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的难度。加之扇面凹凸不平,运笔艰难,要在这尺幅半圆之内,写出凌而不乱的好字,画出浑然天成的好画,并非一件易事。
从书法上来说,折扇扇面书法需谨慎处理扇骨与书写量的关系,周密计算字数,妥善将其安排在扇骨之间的空白处,协调一致,不能前紧后松,或前松后紧。因扇骨高低不平,行笔容易卡顿,一般字体不宜用狂草。又因裱好的扇面,宣纸书画面剩只过半,所以书写时不宜多蘸墨。另外,印章的选择不宜太大,需与扇面上字的大小相协调。
此外,由于扇面上宽下窄的形状,所以在创作时,要做出恰当的安排,由此产生了几种常见的方式:一为充分利用上端,下端不用;二为仅写寥寥几字,利用扇面的宽度由右向左横排书写;三为上端依次书写,下端隔行书写,形成长短错落的格局,避免上端疏朗,下端拥挤,以达到通篇和谐。
宋代以前,很多扇面创作都是书而不画,因为文人皆能书,却未必能画。宋代文人画兴起后,书画共扇的情况开始多起来,历经宋、元、明、清,其发展进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在两宋、明清两大艺术高峰之间,元朝处于一个寂然的低谷,遗失了前代团扇艺术的繁荣,也无新的作为。然而,“至明则折扇大兴,纨扇几无人问”。折扇的异军突起,带动了扇面书画的复兴,并走向了新的巅峰。
清高士奇云:“挥洒翰墨始于成化间。”现在所能看到最早的折扇扇面正是生活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谢缙所作的《汀树钓船图》;明中后期,被称为“吴门四家”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无不创作出大量扇面书画精品,“蔚为吴下人书画扇面之风气”;后来者如“松江画派”“扬州八怪”等都创造出了带有自己独特气质的扇面艺术作品。折扇以其别致的造型吸引了无数丹青圣手,使得曾经盛极一时的团扇书画受到了冷落,“观故宫所藏折扇,无论成扇或扇面帖,为数极多,明贤如沈唐文仇,其精品几不胜数,而纨扇绝少,驯致竟无一件,而清代亦然。”
近代以来,任伯年、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家,都有扇面书画作品。任伯年擅长画扇,从团扇到折扇都留下了不少的作品;齐白石喜在泥金纸扇上作画,所画蚂蚁、蜜蜂生动精细;徐悲鸿虽以画马闻名,但他的扇面花卉也是清新秀丽……可以说,扇面书画已成为中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折扇书画历经了抗日战争炮火的侵扰和“十年浩劫”的扼杀,存活下来的一些瑰宝以令人望而却步的天价重见天日,而许多画家也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历久弥新的领域,重新拾笔在扇面上作画,赋予其新时代的生命力。
魂•“一览乾坤多少事,全付轻摇任笑谈”
在折扇书画逐渐发展和独立之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折扇也脱离了它的肉身,走到了文学艺术作品中去。在清代戏曲作家孔尚任的传奇剧本《桃花扇》中,折扇既是一把打眼的道具,又贯穿了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以及国家兴亡的始末,在作品中挑起了重担:它在新婚之夜作为侯送给李的定情信物出现,寄托著“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的浪漫赞誉;随着复社文人与阉党余孽斗争的升温,“桃花扇”又成为香君反抗强权、保卫自己人格的武器;李香君把“点点碧血洒白扇”的诗扇当作书信寄给侯方域,扇子又成为二人传情之物;张遥星生气地将扇子撕碎扔了一地,撕碎了侯李二人心头最后的念想,使得扇子最终也成为了斩断爱情之路的利剑。此外,“桃花扇”还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是侯李充斥着悲欢离合的波折命运的象征,也是南明王朝兴亡的象征。一把折扇,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在统摄全域中不断地勾起了人们的共鸣和联想,任悲喜在扇子的张合间流动交融。
在其他文学作品中,折扇的身影也十分活跃。《红楼梦》中有许多对扇子的描写,除了衬托锦衣玉食的富贵气象,更重要的是点明了不同人物的鲜明性格。晴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将她身份低微却泼辣刚烈、敢做敢为的性格展露无遗。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破落户出身,每每随一帮狐朋狗友出去胡混,偏要带着一把折扇装点身份,借“手拿洒金川扇儿”来附庸风雅,更显示了他那一副暴发户的做派。在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湖南的扇子》中,主人公来到湖南后,感受到了自身诗意幻想的破灭,以及现实浓重政治氛围的压迫,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蓦然却在一位树下美人手持的半开着的折扇上,重新接收到了他曾在中国诗文中读到过的妩媚和柔情……或是行走江湖,或是裹卷红尘,或是指点江山,一个个身份面目不同的角色,在折扇这怀袖之物的装点下爆发了无穷的生命力,变得更加立体而直透人心。
几千年来,人们在使用和玩赏折扇的过程中,不断提炼著折扇的形式美,更在这富有情感与内涵的诠释和表达中,无形地为折扇增添一笔笔精神之趣,正所谓“一览乾坤多少事,全付轻摇任笑谈”。一把折扇合拢了,便如收拢了“那些盛唐的山水云天,那些大宋的楼阁亭台,那些明清的花鸟虫鱼,还有那些柳体了的和颜体了的象形文字”。
当代散文家汪建中在《中国折扇》中写道,折扇文化在二十世纪末已经“无言而心甘情愿”地收拢了,“与其热闹地打开,不如寂寞地合拢”,免得那流溢的才华与审美受风雨欺辱。折扇闲静的特点似乎与现代都市的喧嚣有着无可调和的冲突。现时最常见的折扇,都是那些来自流水线上、遍布各个旅游景点的毫无灵气的小商品。
然而,折扇的生命力远不会断绝。它只是放慢了张合,等待着下一次蓄力的爆发。在《中国诗词大会》等宣扬传统文化的节目受到瞩目的今天,人们对国学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日益苏醒。而折扇作为如此醒目的象征物,也会吸引人们去挖掘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赏识这悠悠炼扇之路上的又一道风光。
作者:陈宇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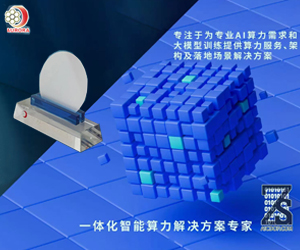




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