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乡愁 余光中的诗篇
《乡愁》作者余光中先生今辞世,享年90岁。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从事文学创作超过半个世纪,一首《乡愁》在全球华人世界引发共鸣。
在台湾文坛中,余光中先生或许是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作家之一。虽然他自称“右手为诗,左手为文”,但大部分人心目中的余光中,还是一位吟著《乡愁》的诗人。
“自八〇年代开放以来,我的诗传入大陆,流行最广的一首该是《乡愁》,能背的人极多,转载与引述的频率极高。一颗小石子竟激起如许波纹,当初怎麽会料到?他如《民歌》《乡愁四韵》《当我死时》几首,读者亦多,因此媒体甚至评论家乾脆叫我做‘乡愁诗人’。许多读者自承认识我的诗,都是从这一首开始。”余光中的文学活动广泛,诗、散文、评论、译书等都有所涉猎。半个世纪以来,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出版了大量的余光中诗集、散文集、批评集……在诗歌上,他不仅被誉为“诗坛祭酒”,而且在六十年内,创作了二十册诗集,约一千多首诗,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高质高产的诗人。在如此丰富的诗歌创作中,“乡愁诗”依然是受人瞩目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香港等地,余光中的“乡愁诗”都广为人知,这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文化具象。这其中的缘由既有内在的,又有外在的,当中还掺杂了许多複杂因素。余光中本人的人生经历与文学修养更是使“乡愁诗”立体化的重要原因。
“游子”的乡愁
“乡愁”,何为“乡”,为何“愁”?
“乡”者,故乡、原籍、出生之地。从狭义上来说,“乡”可以仅仅指代自己的故乡,即出生、生活过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乡愁”是一种私密的、个人的情感。从广义上来说,又可作为两类看待——空间上的“故乡”和时间上的“故乡”。从空间角度来讲,与故乡相对的是他乡,而当我们放大整个空间视角时,故乡的范围也就随之放大了。一个人的故乡是一个村镇,一个城市,一个省份,也可以是一个国家。这往往取决于我们所处的“他乡”。而从时间角度来看,故乡往往交织了岁月的痕迹与时间的记忆,这类不可回溯的事物最终成为人们在今后“求而不得”的执念。而在许多情况下,人所谓的“乡愁”总是将上述事物纠缠其中,难分难解。因此,一个人的“乡愁”往往是复杂多面的。一处故乡,一名游子,万般愁思。
余光中的一生无疑是伴着历史的步伐而前进的。1928年(民国十七年),九月初九的那一天,祖籍福建永春的余光中出生在了南京,因恰逢重阳节,便自称“茱萸的孩子”。他的父母皆受过良好的教育,父母的言传身教与谆谆教诲无疑是他古典文学啓蒙的开端。战争阴影下的儿时生活充斥着动荡与流离,他与家人从上海、香港、昆明辗转来到重庆,最后在四川居住了八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南京,就读于金陵大学。后又逢国共内战,转学厦门大学。接著又来到了香港,在此终是告别了他的大陆。不久,余光中随父母迁居台湾,就读于台大外文系,在这里,他的文学创作受到了前辈梁实秋的鼓励和肯定。到此为止的几十年间,在混乱的时代中,余光中的足迹似乎是踏遍了半个中华大地。
“我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夏天告别大陆的。在甲板上当风回顾鼓浪屿,那彷徨少年绝未想到,这一别几乎就是半个世纪。当时我已经二十一岁,纸觉得前途渺茫,绝不会想到冥冥之中,这不幸仍有其大幸:因为那时如果我更年轻,甚至只有十三四岁,则我对后土的感受就不够深,对华夏文化的孺慕也不够厚,来日的欧风美雨,尤其是美雨,势必无力承受。”
这段话出自余光中为《余光中集》所作的自序——《炼石补天蔚晚霞》,从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到,虽然当时年岁尚轻,恍惚未觉离别之意,但此时的他早已亲身踏过半个中华的山河,感受了历史的风雨,更重要的是汲取了华夏文化的乳汁,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浸染,这不仅为他后来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是为之后的“乡愁诗”埋下了伏笔。
在台湾,余光中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也在这裡与“来自江南的表妹”恋爱结婚。他的生活看起来似乎开始平静展开,但在一九五八年的近一个月间,长女姗姗的出世与母亲的病逝接连而至,不可抗拒的生命的消逝与携着希望的新生一同扑面而来,悲喜之间一时难以言说。而也在这一年,他获得了亚洲协会奖金,怀著复杂的心情,前往爱荷华大学进修一年,开始了他的美国之旅。一九六四年,余光中又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两年,先后在伊利诺、密西根、宾夕法尼亚、纽约四州讲学。一九六九年,他又第三次赴美,被美国教育部聘为科罗拉多州的教育厅外国课程顾问和寺钟学院客座教授。这三次的赴美经历,既是一次与西方文化的亲密接触,也让他深刻感受到了去国离家的滋味。这不仅是从地理距离上所谓的“他乡”遥望“故乡”的情思,更是骨子裡的传统文化的寂寞。这段美国时期对他的影响巨大,他最终选择成为“回头的浪子”,重回古典的怀抱。
一九七四年,余光中来到香港,回到了当初告别大陆的地方。此时正值“文革”,香港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恰到好处的地方。在香港,他度过了十一个年头,也在这裡迎来了创作的盛期。余光中在此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出版了《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紫荆赋》三本诗集。一九八五年,余光中又回到台湾高雄,从此定居于此。
不论是幼时的颠沛流离,还是后来的辗转各地,“乡愁”一词似乎是永远伴随其身的。从前是家乡的游子,后来是大陆的游子,再后来是华夏的游子。即使后来能够重回故地,时间却从不会给人重现时光的后门。余光中的“乡愁”理所当然是多重的、复杂的。“乡”之一词,于他而言内涵太过庞杂,因此无论身处何方,他永远是一名怀愁的游子。
文化的乡愁
提起“乡愁诗”,首先要弄清楚什麽是乡愁诗。上文中提到,“乡愁”的概念无疑是複杂多面的,而余光中本人所谓的“乡愁”更是如此。对于他的“乡愁诗”的具体数目,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确切的数字,因此,我们不妨将他的“乡愁诗”的范围放得宽泛些。除去一些明确提到或出现类似“乡愁”字眼的诗歌,如《乡愁》《乡愁四韵》《白玉苦瓜》等,《寻李白》《戏李白》《水仙操》《湘逝》等有关“故乡”山河、文化的诗歌不妨也看作是“乡愁诗”。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著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著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髮/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歴四十三年。”(《从母亲到外遇》)
正如现在许多人所意识到的,余光中的“乡愁”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或者是时间意义上的“乡愁”。他的“乡愁”还在深深凝视著深厚绵长的华夏文化,是一种融合了地理与历史的“文化的乡愁”。“ ……中年人的乡思和孺慕,不仅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不仅是那一块大大陆的母体,也是,甚且更是,那上面发生过的一切。土地的意义,因历史而更形丰富。”(《白玉苦瓜》自序)
焦桐对余光中的“乡愁诗”的发展分佈做了如下的分析:“早期诗作较少涉及乡愁母题,仅《五陵少年》中的《五陵少年》和《春天,遂想起》。大致从《敲打乐》开始升高乡愁母题,到了《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拔上了高峰,《梦与地理》以降,题材上的‘本土化’愈益明显,第十六本诗集《安石榴》(1996年)各种题材并陈,‘台湾心’的比重甚于‘中国结’。大致上,愈晚期的作品《乡愁》指数愈低,《安石榴》中勉强列入《乡愁》之作只有《宜兴茶壶》《金陵子弟》《召魂》三首。起初,《乡愁》还纸是怀念,<坐看云起时>追忆江南,意谓目前生活的台湾,两个母亲分别在海峡两边召唤。后来,《乡愁》的咏歎,变奏为感时忧国的沉吟,对人的关注远远凌驾于对国的信仰。”余光中的早期诗作较少涉及“乡愁”主题,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愈晚期的作品乡愁指数愈低”的原因,或许是因为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互通,回到大陆的次数增加,地理上的“乡愁”之感反而不再如从前那般,但是,时间意义上的“乡愁”和“文化的乡愁”却是依然存在的。
诗化的乡愁
余光中早年写古典诗,后又转写现代诗,然而,他的诗其实可以算得上是现代的躯壳中流著古典的血液。有意思的是,他年轻时曾攻读外文系,后又多次赴美学习交流,但最终回首重拾东方的古典。在文学上,尤其是在诗歌上,他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这就是余光中诗歌的迷人特质,后又引来不知多少人来研究。民国时期走来的文人,不说在中国古典文学上造诣深厚,也大都于此系统学习、深谙于心,而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他们又匆匆奔向西方文化的领土,中西文化的碰撞总在有心人的笔下绽放出耀眼的火花。这点深刻体现在他后来所主张实践的“新古典主义”中。而“乡愁诗”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方式,一方面是对古老东方大地的追忆,另一方面是对悠久华夏文化的怀恋。余光中作为现代人,取自中国古典艺术的血液,以现代的诗歌形式来表现其内容,这就在内容和形式上完成了一个古与今的沟通融合。
余光中“乡愁诗”的诗歌语言兼採现代西方的逻辑条理和东方古典诗歌的简洁浑成,其中又不失口语的亲切自然。诗歌中所出现的意象丰富,我们可以发现,历史意象、地理意象、文化意象都是他笔下常常出现的。其中又以李白、杜甫、长江、长城、艺术品等人们所熟知的极富文化气息的人、事物为代表。
以他的《白玉苦瓜》为例:
“似醒似睡,缓缓的柔光里
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
一只瓜从从容容在成熟
一只苦瓜,不是涩苦
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莹
看茎须缭绕,叶掌抚抱
哪一年的丰收像一口要吸尽
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
完美的圆腻啊酣然而饱
那触觉,不断向外膨胀
充实每一粒酪白的葡萄
直到瓜尖,仍翘着当日的新鲜
茫茫九州只缩成一张舆图
小时候不知道将它叠起
一任摊开那无穷无尽
硕大似记忆母亲,她的胸脯
你便向那片肥沃葡匐
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
苦心的悲慈苦苦哺出
不幸呢还是大幸这婴孩
锺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
皮靴踩过,马蹄踏过
重吨战车的履带辗过
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
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
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
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
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
饱满而不虞腐烂,一只仙果
不产生在仙山,产在人间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腕
千眄万睐巧将你引渡
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
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
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
这首《白玉苦瓜》被认为是余光中“乡愁诗”的代表作之一,“白玉苦瓜”是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的一件精美艺术品。整首诗借咏物——白玉苦瓜,来抒诗人之情。诗的开头,首先描述讚美了白玉苦瓜的外表、色泽、造型之美,表现了艺术的永恒;接着由苦瓜之美进一步深入到苦瓜之苦,“皮靴”“马蹄”“履带”象徵中华民族所受的苦难,体现出中国意识;最后将白玉苦瓜与诗人自况融合,表明诗人经受苦难的洗礼,生命意识和诗艺的永恒流转于心。一件白玉苦瓜,引出了多层的内涵和象徵,颇有中国古典诗歌和文字弹性之美的影子。
另外,这首诗被收录的诗集便是以《白玉苦瓜》为名。“书以《白玉苦瓜》为名,也许是因为这一首诗比较接近前面所悬‘三度空间’的期望吧。”余光中所谓的“三度空间”,指的是“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纵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而这三点都在这首诗中很好地体现了出来:白玉苦瓜的身上齐聚了历史感和地域感,这件艺术品既留下了时间的痕迹,本身又远渡海峡,见证了历史与地域的发展变化;而诗人站在现实裡,成为了历史和地域的守望者。
当人的情感借由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再被人们所感知,就形成了二度创作。余光中的“乡愁诗”是诗化了的乡愁,当人们读他的诗,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其中时,所产生的情感又是不同的。正是因为“乡愁诗”内容和情感的丰富性,使得人们从中自觉或不自觉抽取的内涵富有了弹性。从古典到现代,又回归古典,从地理到历史,再到文化,从个人到国家,又上升到生命感受,余光中“乡愁诗”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探寻“乡愁”背后的灵魂
余光中的“乡愁诗”在两岸四地流传甚广,他在华人世界的知名度之高,各类相关诗集的出版热潮与“乡愁诗”的研究热度一直难以消退的现象,使人不禁产生好奇。余光中“乡愁诗”的流传与接受之广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 诗歌语言特色和传播方式
余光中被认为是艺术上的“多妻主义”,他的诗歌题材与风格多变,因此很难归纳出一个统一的特色,但分析他流传较广的几首“乡愁诗”,如《乡愁》与《乡愁四韵》,就会发现这类乡愁诗的语言简洁质朴却又不失意趣。尤其是在大陆广为流传的《乡愁》,让人不禁联想起人们自古至今都广为传诵的李白的《静夜思》。余光中认为优秀的现代中文,应有“文言文的简洁浑成,西语的井然条理,口语的亲切自然。”诗歌质朴易懂,同时也就扩大了接受者的范围。同时,除了诗集这一传统的传播方式外,余光中的“乡愁诗”有相当一部分被谱成了歌曲,而他也十分重视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他在《白玉苦瓜》这本诗集的后序中提到“凡是成功的现代诗人,没有一位不是在音乐性上别有建树的。”他认为歌“是现代诗大众化的一个途迳”。他的《乡愁四韵》《民歌》等诗都曾被谱成了歌,广为传唱。此外,随著现代网络媒体的发展,不仅仅是“乡愁诗”,其他文学作品的传播也越来越方便。
二、 现实原因与抽象情感的共通性
文学作品的传播离不开现实环境。不论是国人背井离乡,海峡两岸遥遥相望,还是海外华人隔海相对,“乡愁诗”都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人们情感表达的需要。而随著国家的开放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离开故土,“乡愁诗”的生命力也在延续。“乡愁”这一母题几乎存在于各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中,这是人类远古以来就存在的情感。就如同现在的人们青睐李煜的词中的抽象情感,余光中“乡愁诗”中抽象出来的“乡愁”情感具有共通性,这也是其“乡愁诗”接受人群广泛的原因。
三、诗歌传统下的民族情感和文化共识
“乡愁诗”的诗歌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古典诗词。中国古代诗歌中以“思乡”为主题的诗词数不胜数,李白的《静夜思》、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张籍的《秋思》、王维的《杂诗》、纳兰性德的《长相思》等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故土之思”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早已是文学作品中的主角之一,而这一切都要归因于整个中华文化背景下人们所持的价值观念。而在传统观念里,“家”与“国”的关系又是千丝万缕、息息相关,“故土之思”往往会引申出“故国之思”。在这个基础上来分析余光中“乡愁诗”的流传情况,就不难理解人们的态度了。正是因为契合了同一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再加上诗人的人生遭遇的影响和自身古典文学修养的助推,造就了其“乡愁诗”的接受现状。纵观整个华人世界,虽然口音各异、地域不同,但骨子裡的华夏文化的印记却是难以抹去。所以余光中虽写自己的“乡愁”,但却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
余光中以自身的人生经历、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酝酿写就“乡愁诗”,其“乡愁诗”富有弹性的内容与形式,成就了他与众不同的诗歌风格。而“乡愁诗”的广泛流传,又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永恒的乡愁”,不仅仅是于诗人而言,“乡愁诗”更让我们看到了诸多炎黄子孙绵长难消的乡思。
文:熊璐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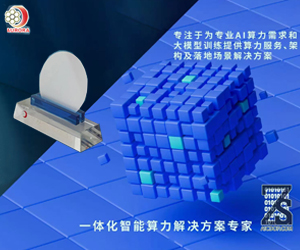




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