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云端的自由灵魂——三毛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的港台文学传入中国大陆,而此时的大陆文坛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寻根文学”,沉郁压抑的风格都不适于渴望新鲜空气的大众读者,相反,或纯爱、或侠义、或新奇的港台文学则为刚刚经历了“文革”的人们注入了一股清流,引起了人们对港台作家的热情追捧。三毛的作品就在70年代末传入大陆,她那幽默风趣的语言,自然洒脱的文笔,充满异国浪漫色彩的见闻,迅速受到了大批读者的喜爱,进而出现了“三毛热”。
三毛的作品以自身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大量纪行散文为主, 如为人熟知的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温柔的夜》《万水千山走遍》等,此外还包括小说、剧本等。其中,她创作的剧本《滚滚红尘》获得了台湾金马奖八项大奖,却也成为了她的遗作。三毛最先为大陆人们所接触到的作品是台湾电影《欢颜》中的插曲《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这首由她作词的歌曲仿佛不是为电影创作,反而更像是为三毛自己而存在的,寄託了她对自由的流浪生活的怀恋。
三毛的人生因她的文字而为人们所熟知。她与荷西的爱情、她的撒哈拉、她的软弱与坚强、欢喜与悲痛、感动与忧郁,在读者面前仿佛已经被清清楚楚地剖开来了。人们常常将文字里的三毛臆想成现实里的三毛,痴迷于她浪漫神奇的异国经历,感慨于她与荷西真挚的爱情,她是这样一位“不现实”的女子!与许多普通人的生活相比,三毛无疑是奔波匆忙的,她就像天上任卷随舒的云,永远没有固定的目的地,随性自然地随风雨去、随风雨归,身躯和灵魂永远在前往自由的道路上。
“少年维特”之二毛
“当三毛还是二毛的时候,她是一个逆子,她追求每一个年轻人自己也说不出到底是在追求什么的那份情怀……”(《当三毛还是二毛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在经历一些事情后得到成长转变,三毛也不例外。在接受撒哈拉沙漠洗礼之前的三毛,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跟今日健康进取的三毛有很大不同的二毛”。三毛出生于一个家境良好的律师家庭,小时候的她无疑是一个异于常人的古怪孩子,脑子里充满了稀奇古怪的想法。与同学们的高远志向不同,三毛希望长大后做一个幸福的“拾荒者”,为此,她还受到了老师的批评。三毛聪明却也敏感,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和天赋,五岁半就开始看《红楼梦》,初中时更是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着,这为她以后进行文学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毛上学的时候语文成绩极好,数学成绩却极差,甚至少有及格。为此,她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将考试中的数学题目背下来,而接连几次数学考试都得了一百分的她引起了数学老师的怀疑,老师断定三毛作弊并在她的眼睛上用黑色墨水画了两个黑眼圈,让她在众人面前罚站。这段经历,无疑深深伤害了一个敏感孩子的自尊心,而这对三毛之后的性格影响巨大。初二的时候,她由于病痛休学在家。父母为了开导三毛,开始鼓励她学习喜爱的写作和美术。三毛先后跟随顾福生、邵幼轩两位画家习画。此后,文字和艺术果然伴随了三毛漂泊的一生,并重新建立起了她与外界的联系。收录于散文集《雨季不再来》的《惑》,讲述的是“我”迷失在了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珍妮的画像》的插曲中,虚拟的珍妮和现实里的“我”有一种微妙的互相吞噬的关系,“我”被医生认为是精神出了问题,虽然在进行治疗并一直受着父母的关爱,但珍妮与“我”的联系却始终存在,而“我”也渐渐迷失在了珍妮的歌声中……这部作品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现实里的三毛、“现实”里的“我”和虚幻中的珍妮这三者相互抗拒又彼此牵引的关系。整篇文章情绪激烈,仿佛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苦闷钳制于身,以至于父母的爱也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惑》中的“我”固然不能等同于三毛本人,但从中却也能看到当年挣扎于病痛和精神困境的影子。《秋恋》讲述一对青年男女在异国相遇,一见锺情后随即各奔东西。《月河》描写女孩林珊对男孩沉的爱恋,同样是一面之缘,便深陷其中。《极乐鸟》中朋友S的自杀使她激愤不已。《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描绘一个夏日的早晨,一群朋友重游故地,重逢与离别,回忆与现实,都交织在一个早晨中,具有别样的清新美感。
《安东尼•我的安东尼》里背井离乡的“我”帮忙照顾一隻名叫安东尼的鸟,并对它产生了感情,然而安东尼在一个雨夜由于“我”的疏忽死去了。三毛这个时期的文章截然不同于之后在撒哈拉的明朗风格,失学与病痛以及接触到的生活环境的限制,使得三毛笔下的主人公大都细腻敏感、多思孤独。而之前学画的经历使得三毛对艺术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她的故事里常常会涉及到绘画,如《秋恋》和《月河》中的主人公便都与美术有关。
三毛如同所有青春期的少女一样,对情感有一种微妙的掌控,这个时期的作品大都充斥着强烈而又隐忍的感情、大段心理活动的描写,以及“青春期式”的忧郁。虽然不免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偏向,但还是能看到“二毛”对文字的敏感和情感的把控。她虽然时而失落悲伤,但是仍然在思考追求人生,而尤为重要的是她真实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少女的真挚情感。就如三毛所说:“我之所以不害羞地肯将我过去十七岁到二十二岁那一段时间里所发表的一些文稿成集出书,无非只有一个目的——这本《雨季不再来》的小书,代表了一个少女成长的过程和感受。”(《当三毛还是二毛的时候》)
少年时期的三毛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探索,外面的世界仿佛只是她丰富情感的陪衬。我们不能说此时的三毛不现实,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个时期,而这是一个新鲜的人对世界、人生、感情的自我思考阶段。相对封闭的环境和有限的交流,使得三毛不得不从精神世界寻求慰藉,她的聪敏和孤介促使她的认知不同于寻常人,这也就埋下了三毛超脱红尘、游离人间的伏笔。从这里,三毛自由的内心开始奔向广阔的世界。
浪漫的异乡人
三毛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纵观她的一生,似乎永远在辗转各地。1943年,三毛出生在重庆。1948年,她随父母来到了台湾。1967年,三毛又孤身一人前往西班牙留学。此后她又前往德国,在歌德学院学习德文,紧接着来到美国伊利诺大学法学图书馆工作。1970年,回到台湾在大学任教,后因未婚夫猝逝,再次离台,回到西班牙。1973年,终于来到心心念念的撒哈拉沙漠并与深爱她的荷西结婚。由于政治内乱她离开撒哈拉沙漠后,来到加纳利群岛。1979年,荷西因潜水意外离世,三毛再次回到台湾。此后,她又相继去往中南美洲、大陆等地。如果说三毛人生一开始的漂泊不是由她所决定,那么之后的“流浪” 生活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每一个地方于三毛而言都是“异乡”,但是她的包容和友善却能消磨与当地人的隔阂;每一次停留最后都令人依恋,但她的“故乡”永远在远方。“人生是多么美好啊!因为下一站要发生什么事情,完全不知道。所以我说,我喜欢出发。”(《远方的故事》)关于“流浪”的原因,三毛自己解释为:结束了一个地方的学习工作后便去往下一个地方。不同于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物质上的安定和外界环境的稳定,三毛精神上的满足来源于内心的充实与自由,于是她选择了漂泊。
“流浪”的三毛像是随心所欲的河流,依着地势流往前方,既享受奔流直下的刺激,也欢喜缓缓流淌的悠閒,一路上的风景倒映在她的眼中,她永远没有固定的目的地。三毛偶尔也有漂泊在外的孤独感,但不同于饱尝漂泊之苦的游子,她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人生曼妙之路的探索欲让她对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荷西的爱情是她人生旅途的星光,他的等待与真诚换来了三毛的回应。“我一生的想望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公寓,里面有一个像你一样的太太,然后我去赚钱养活你,这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梦想。
(《一个男孩子的爱情》)这个大胡子西班牙人外表粗犷,却有着柔软细腻的内心,在三毛决定前往环境恶劣的撒哈拉沙漠时,荷西先她一步来到沙漠,找到工作,租好房子,打点一切,迎接心爱的人到来。他们的婚姻简单朴素,但内心充盈饱涨。荷西之于三毛,是知己,是爱人,是朋友。他的陪伴使三毛的旅途有了不一样的色彩,记录两人生活的《撒哈拉的故事》简单、快乐、饱含热情,以完全区别于之前作品风格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这部作品,无论是在人生中还是文学上,都是三毛新的开始。
三毛的异国漂泊经历,给她的性格和眼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在自身成长变化的同时,她的作品也“长大了”。首先,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作品内容的丰富。三毛初期的作品主要围绕个人的内心波动,注重个人体验,而从《撒哈拉的故事》开始,我们能看到三毛笔下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娃娃新娘》中撒哈拉十岁新娘姑卡的出嫁和《哑奴》中留存至今的奴隶制度,表现了三毛和撒哈拉各自所代表的两个文明之间的碰撞。
《死果》里害人性命的符咒和《寂地》中沙漠流传的鬼魅“脸狺”,都是遥远国度中的奇闻秘事。《哭泣的骆驼》中三毛亲身经历了撒哈拉沙漠里惊心动魄的政变。《五月花》里她又与狡诈无赖的老板斗智斗勇。三毛的经历为她的作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读者带来了一场浪漫奇幻的异国之旅。其次,则是三毛作品风格的转变。三毛的早期作品多愁善感、感伤忧郁,而在经历了时光和旅途风霜的洗礼后,她的文字变得更加成熟乐观,物质的匮乏也挡不住她对生活的热爱,创作手法也从早期注重心理描写转变为平铺直叙的白描,三毛用简单智慧的语言将她多彩的生活娓娓道来,她成了大众读者印象里的那个“三毛”。三毛由初期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变为身体力行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广阔的环境,多样的人生,丰富的见闻,进而给三毛带来了不同寻常的体验,她骨子里的叛逆孤僻被旅途的风沙打磨圆润,她的身体和灵魂也变得“像空气一样自由”。
生命的探寻者
三毛是一个基督教徒,但她也看佛经,她的行事有道家逍遥自在的风范,观念里又有着儒家的道德感,很难说她到底秉持着哪一种信仰,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短暂而又丰富的一生中,始终围绕着爱与人性去探寻生命的真谛。
撒哈拉对于三毛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不记得在哪一年以前,我无意间翻到了一本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里,正好在介绍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式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大地。”(《白手成家》)在这片贫瘠的沙漠里,自然条件恶劣,出行用水都极为不便,但三毛却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由于远离现代文明、城市喧嚣,人仿佛变得简单了起来。在三毛眼里,撒哈拉沙漠的人们是真实可爱的,他们在寸草不生的沙漠里,生出了生命的喜悦和爱憎。《哑奴》中被人瞧不起的哑奴在撒哈拉地位低下,却有一个温暖的家,他深爱着他的妻子和孩子。
《芳邻》里常常向三毛借东西的撒哈拉威人用她的红药水装饰打扮自己,唱歌跳舞。《爱的寻求》中被欺骗的年轻撒哈拉威人沙仑执着于远方虚幻的爱情。《沙巴军曹》里与撒哈拉威人有血海深仇的军曹在危险时刻最终选择了牺牲自己来保护几个撒哈拉威孩子。三毛在撒哈拉所看到、接触到的固然不全是如此动人的事物,人性也有丑恶的一面,但三毛选择了关注另一面。她生活在撒哈拉威人中间,和他们做朋友,同他们一起吃骆驼肉,极度荒凉的环境孕育了极度坚韧饱满的鲜活生命,她身处其中,然后了然于胸。
三毛将常人所看重的金钱、地位、学历等外在事物看成是人生的束缚,所以,她看到了撒哈拉沙漠超脱世俗的一面。而在她另外的旅途中,各种各样的经历也一次又一次地触动到她。在《温柔的夜》中,三毛遇到了一个向她数次乞讨两百块来买船票的流浪汉,三毛认为他是个骗子而多次拒绝,最后发现原来他真的是陷入困境,为此而感到羞愧内疚。
《故乡人》中,三毛在陪朋友去墓园时不经意发现了一座刻着中国字的墓碑,想到自己和他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故乡人,内心触动,此后她时时去探望这位客死他乡的同胞,而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这篇文章居然找到了逝者失联多年的亲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三毛和荷西在遥远的加纳利群岛上偶遇了一位漂泊的卖手工艺品的日本青年——莫里,莫里的热情善良感染了三毛和荷西,他们请莫里来到家中吃家常菜,给他送食物,三人在异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这些在遥远异国的经历,可以看到三毛的善良、悲悯,对人性闪光一面的重视。“这种人性的光辉面,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加以表现的,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昨日•今日•明日》)
但在三毛自己的人生中,精神上的孤独感和迷惘一直挥之不去,除却为读者所熟知喜爱的浪漫的流浪之旅,她自己有着三次自杀的经历。尤其是荷西去世后她所经历的悲怆失落,让人们不得不思考那个活在文字中的“三毛”和真实的三毛的对等性,或许那个活在人们心里的是一个她自己过滤后了的三毛。她将人性推崇到了理想的高度,但事实上理想与现实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歧,从而导致悲剧,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三毛或许在离开中找到了精神的永恒和归宿。“无所谓长短,无所谓欢乐、哀愁,无所谓爱恨、得失……一切都要过去,像那些花,那些流水…… ”
多少年后,依然有人喜爱三毛,她的传奇经历和浪漫爱情仍然让人津津乐道,但更重要的是三毛对生命的执着,对自由的追寻,代表了人们被种种事物束缚的内心的渴望,因此,才有如此多的人被三毛所感染。三毛是一个放大镜下的我们,每个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的人,都可以从三毛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她是现实世界里的流浪者,红尘里的边缘人,一个“不切实际”的漫步云端的自由灵魂。
文:彭万隆 熊璐璐
欢迎关注《东方文化》微信公众号(ID:dfwh_h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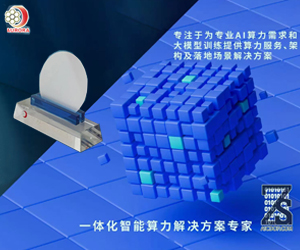




评论已关闭